
今天下午,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享年75岁。他的家人透露消息后,文学圈内一片哀悼缅怀。
雷达先生是《文汇报》的老朋友,多年来在文汇报上刊发了多篇文学评论,影响广泛。作为贯穿新时期文学40年的当代重要批评家,雷达是敢于直面创作症候、善于辨析审美变化的观察者。雷达最早发现并评述了“新写实”,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命名;他跟踪共和国当代文学的步伐,对重要作家作品和重大文学现象,都做了充满生命激情和思想力量的及时回应。
批评家白烨曾说:“雷达对作品的精幽、微妙之处,感觉敏锐,捕捉敏捷,表达审美体验的文字也颇富诗意,暗中内含的逻辑引线与思想引力,常常能把人们由美的感悟引入灵的顿悟。”作家贾平凹赞赏:“对雷达的评论,可以用‘正’‘大’来比喻。‘正’,是他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经历的事多,众多文学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他都参与或目睹。他的评论更多的是蕴涵着传统的东西;他的文字代表担当,代表了正,代表了生活,代表了权威。”
雷达原名雷达学,1943年生于甘肃天水,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著有论文集《民族灵魂的重铸》《思潮与文体》《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等,散文集《缩略时代》《雷达散文》《皋兰夜语》 《黄河远上》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今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雷达批评文论集《雷达观潮》。著名批评家李敬泽为该书作序,雷达写了后记。经出版方授权,特发以表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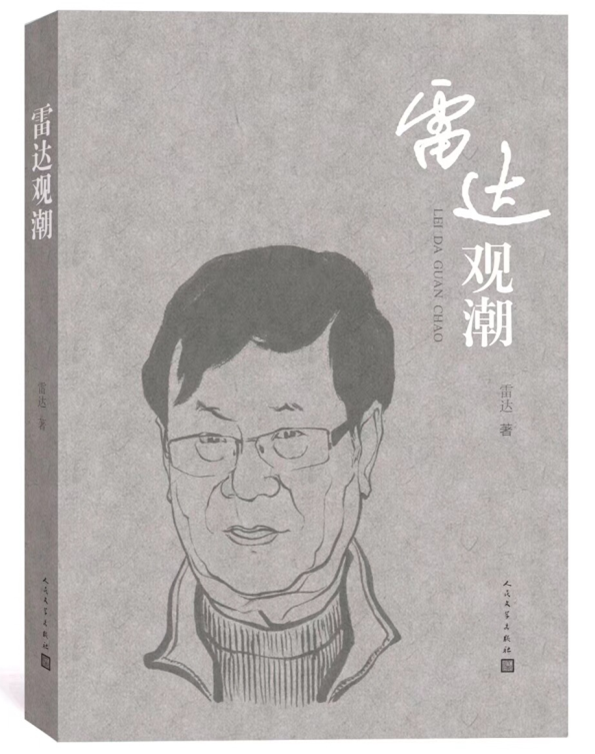
《雷达观潮》
雷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文/李敬泽
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什刹海还是一片冬天可以滑冰,夏天可以游泳的湖。彼时我还没有想过当个评论家,日子悠长清简,须忙出很多闲事打发它。比如夏天里,骑自行车,每日从安贞桥晃到什刹海南岸,岸边一棵垂柳下脱衣,跳进湖里,向湖心小洲游去。
那时的什刹海,每日岸边总有十几个泳客,以北京大爷居多,游几个来回,上得岸来,三五人袒腹相对,各持一瓶“小二”,一包花生米,半斤猪头肉,蛙鸣蝉噪,清风微雨,湖海边把天下事论得风起云涌。
在那里,常见到雷达老师。
当然,此前也是认识的。雷达之名如雷贯耳,彼时他正当盛年,激扬文字,论断天下文章,其气盛,其言宜,小子如我,望之如天边之云。忽一日,水淋淋爬上岸来,一抬眼看见一人,看来看去,莫非是雷达?只觉得他是按下云头,落到了凡间。
在湖边,和雷达谈了些什么,现在全忘了。肯定没谈过文学。或许是,谈谈身体,谈谈水,谈谈他甘肃老家的土和山。
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一天,雷达老师来电,命我为他的新书作序。雷达之命不可违,但心中实在惶恐,点一斗烟压压惊,心想,写就写吧,雷达是师长,又是忘年之交,太熟了有些郑重的话平素反说不出口,正好借这一篇序,略表我对雷达老师的敬意。
90年代以来,批评家分了两种,一种是学院的或学术的,另一种是现场的或实践的。个中分殊一言难尽。但若说到后一种,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雷达。
雷达是现实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但绝不仅仅如此,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巨大转型中,雷达执着而雄辩的论证,为现实主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对雷达来说,现实主义是信念,但信念不是教条,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推动变革和创造的实践活动,它不是为了规范世界,而是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
雷达正如“雷达”,他从来宽阔灵敏,随时向着新鲜经验开放,谛听天地消息。多少年来,我不知读了雷达多少文章,不知听了他多少次发言。我当然不是每次都同意他的观点和论断,但是,我从来不曾认为雷达是停滞的封闭的,他从来不曾失去敏锐的现实感,从来不曾失去与时代、与生活、与当下的文学写作对话的能力,他从来是勇猛精进的,他是不老的猛兽,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当他为他之所是申辩时,机敏周详,令人折服,当他向着他之所非而争辩时,他是谨慎的,又是严正的。
他不是不知道,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几番更新换代,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有广博活跃的知识兴趣,但他从未放弃、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原则和方法,对他来说,这关乎文学的和批评的本质,他当然不拒绝方法与时俱进的丰富和扩展,他一直为此做着艰辛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他从未动摇他的原则——他常常让我想起哈罗德·布卢姆,另一个倔强、固执的老头儿,他们之所信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在捍卫所信时的自信、坚定和权威却非常相似。他们都在急剧变化的时世中守护着传统并赋予传统以活力,他们的气质都是既强健又忧伤——是的,雷达竟是忧伤的,他有孩子般的脆弱和天真,在他的底部更是暗藏深悲,唯其如此,他的所信才获得了富于张力和深度的生命经验的支持和充实,他所捍卫的才不仅仅是理论的教条,而是人为争取自由、真实、善美的全部历史斗争和文学表达。
——正因如此,雷达始终是在现场的批评家,作为同行,我时常惊叹他的阅读之广、他的思考之深。他是正心诚意的,是从不苟且从不凑合的。我想他不是不知疲倦,我都常常替他感到累,但是,我想我是懂他的,我能够理解像他这样一位批评家永不衰竭的激情。他对自己有严苛的要求,他肩负使命,他那一代批评家的心里都曾有过来自“别车杜”的召唤,而雷达,他把这种启示和召唤变成了个人持守不渝的使命。
也正因如此,雷达成为了对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清晰的、可以明确辨认的影响的批评家,他有力地参与了文学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回应,有力地参与塑造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貌,由此,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传统的强大活力。
20多年前,在什刹海,我曾和雷达一起游泳。水深不知底,阴险的水草有时会蓄意拂过身体。每年夏天,这里都会有人溺死,我知道这是危险的,惊慌和恐惧会忽然攥住你的腿、你的心肺。这时,在恐惧的时候,我看见前边,雷达在游着,他从容安然,他如同湖心之洲。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雷达在文学批评中如同地平线、如同海岸线,对我来说,无论走得多远、游得多深,抬头看,雷达在前边,回头看,雷达在岸上,这时,心里是踏实的。
为此,感谢老师雷达。
谨序。

文/雷达
我不喜欢雷达这个名字。我是个喜欢耽溺于审美的人,“雷达”给人一种工具化或科技化的,甚至窥探什么的感觉。但是,这由不得我。1943年我出生时,天水新阳镇王家庄雷家巷道里,已经有了雷嗜学、雷愿学、雷进学、雷勤学等一大群人出世,全是“学”字辈,雷字和学字都是固定的,只能动一动中间那个字。于是,母亲采用了我父亲给我起的小名“达僧”中的达字,就有了大名“雷达学”的我。 小镇人哪懂得雷达为何物,到上高中时,忽然有一天大家都开始叫我雷达了,因为他们知道了雷达是什么器物。1978年进入《文艺报》,同事都说干脆叫雷达吧,那个学字有点儿累赘。我听从老大哥们的建议,于今已四十年矣。我曾试图反抗,企图改为默雷,还想着改为春风啊,秋雨啊,夏月啊,冬雷啊。一位相熟的老作家说:你拉倒吧,现在人们知道你已属不易,你一改得从头开始喽。噢,是吗。2014年,《文艺报》邀我开个专栏,我脱口而出说,就叫“雷达观潮”吧。看来似乎我又是认可这个名字的。
这本《雷达观潮》是以我近年来在《文艺报》开设的“雷达观潮”专栏文章为主体的。我力求做到,人虽然老了,思想尽量不老化,甚至要有锋芒;要求自己决不炒冷饭、说套话,要使这些文章密切结合创作实际,提出一些真问题、新问题;诸如现在书中的,“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表现”“代际划分的误区”“文体与思潮的错位”“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文学与新闻的纠缠与开解”“‘非虚构’的兴起”“今天的阅读遇到了什么”“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等等,思想还算活跃,也不失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启发性。这自然算不得什么,但在当前“缺少问题”的语境下,能做到这个程度,对我来说,也不容易啊。
这本书还选择了一批典型的作家作品评论以实证之,从汪曾祺、高晓声,到王蒙、铁凝、莫言、张炜,再到张贤亮、浩然,再到“陕西三大家”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再到刘震云、雪漠等,试图通过他们的代表性面目,勾画出一条富于表情的当代文学画廊。
其中选用了几篇80年代的评论文本,因为奇怪的是,今天读来并不过时,反而有一种欢欣与鼓舞的调子。例如,我翻出一篇早期研究汪曾祺的长文《使用语言的风俗画家》,我都有些惊讶,其中对汪老的几篇小说的分析,还有点精彩。现在评说汪老,已成为显学和时尚,没有人认为我跟汪老有何瓜葛,也不认为我有什么见解,但汪老不是这样。80年代初的一次政协礼堂的聚会上,我的文章刚发表不久,汪老主动走过来说,你是雷达同志吧,那时我才三十多岁。汪老还主动送我一幅字加画。当时还有点纳闷,现在想来,汪老真是多情之人哪。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参与者、研究者,我提出过“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才是新时期文学主潮的观点;我最早发现并评述、归纳了“新写实”的思潮;我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命了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各个时期审美趋向的宏观辨析和症候分析,还有对当前文学的创作症候之分析,构成本书另一些内容。
这一切都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抱憾的是,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做,回首平生,我倒真的是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批评者,心头涌满了复杂的感受。让这本书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份精神档案存留着吧。
文汇记者:许旸
编辑制作:许旸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