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似乎谁家都有一个;她面目模糊,往往是文学作品中的配角……但在作家任晓雯最新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里,这位“弄堂深处的母亲”向人们走来,一步步置于文学聚光灯下——宋没用不再是遭人嫌弃的幺女、陷于琐碎的妇人、被儿孙忽视的老母,她的名字,她的人生,都在文字中留下抹不去的印记。
日前,作家任晓雯、评论家吴亮、张闳、木叶亮相沪上思南读书会,探讨《好人宋没用》对一位默默无闻母亲的塑造。小说讲述了苏北女性宋没用艰辛打拼、立足生根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五个儿女……她经受种种风浪,顽强生活着,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
“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后,我做了庞大的资料库。小说里呈现出的风物、服饰、器皿等细节,都是筛选后经由想象力再度黏合。”任晓雯谈及创作说,宋没用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仍是好人,因为哪怕身处最黑暗时也没有害人,保住了底线,她的身上有出于本能和直觉的人性善意之光。

“宋没用,1921年出生,这也是我母亲出生的年份,我的母亲也姓宋。要不是任晓雯的写作,这样的母亲可能连一句话都无法留下。因了《好人宋没用》,如此精准、冷静、中立、不厌其详的细节,她们得以存活。”吴亮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小说不是“给”,一股脑地“给”是无视读者。而《好人宋没用》没有“给”太多东西,更多是与读者产生对话。
“我能闻到小说里的气味,仿佛置身于人物的室内场景,看到他们就在我身边说话,人物对话非常精彩。大量的简短句子,会迫使你停顿,让你回头再琢磨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吴亮评价,《好人宋没用》的笔调很冷,但和卡夫卡概念化的冷不一样,里面有悲悯,但没有同情,更没有廉价煽情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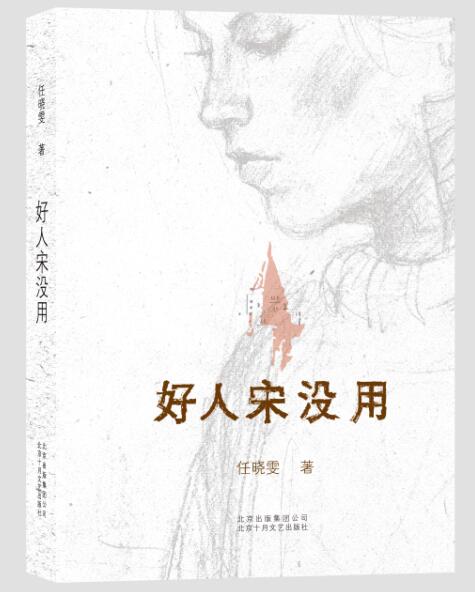
《好人宋没用》
任晓雯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评论家张闳说,《好人宋没用》是对每一个普通生命的关注和肯定,让人联想起莫言小说《欢乐》里齐文栋的母亲,“都是老得已经不行了,像‘破抹布’一样的母亲形象。儿女们亲眼目睹她们的衰落,在被牺牲的一生里,她们置身历史宏观维度显得渺小,但对子女和一个家庭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没有她们,就没有我们。因此,这类母亲形象值得文学界重新考量和关注。”
在张闳看来,情节离奇、惊险或跌宕起伏的故事,诚然会吸引更多读者,但对承载故事之容器的语言质感、色彩,才是好作家更应关注的,《好人宋没用》力求通过简洁叙事来呈现文章气息和现场感,这样的小说相当难得。

评论家木叶谈到,《好人宋没用》书名很微妙,既是“好人”又是“宋没用”,有点矛盾修辞。“这部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有两点是人类理性无法完全解释或框定的,一是道德,一是死亡。《好人宋没用》恰恰把这两种元素糅合在一起展开解读。主人公宋没用,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里凸显出寻常人物的生老病死,让读者看到女儿、妻子、母亲三个身份是如何在一个女人身上集聚的。”木叶发现,小说里多次写到死亡,但即便是一些污秽的存在,作品也是点到为止,没有刻意渲染苦难,“这是一个好作者心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延伸阅读【创作谈】
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经历壮阔的内心风景
文/任晓雯
宋没用,苏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普通不过的老太太,似乎谁家都有一个,耳聋、多话、皱皱巴巴。她是我《南方周末》“浮生”系列里的人物。两千字意犹不尽,便写成了长篇。
上一部我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九年前的《她们》,写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这样的写作,缘于某种传统的影响,以为一部厚重的作品,最好是史诗性的,或者地方志式的。它们通常有着与“厚重”相符的篇幅,描述一段中国历史,一方风土人情。
但我渐渐看到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遮盖了人。我们记得“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书写了某某历史或者地方”,而被书写的某某历史和地方里的人,却是面目模糊的。他们被动地接受苦难,在历史的漩涡里盲目打转。他们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究其原因,或许并不存在复数形式的“她们”,“他们”和“我们”。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
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没用》的写作,就成了从“她们”到“她”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没用是被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她“没用”,子女也认定她“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荫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
宋没用属于刻板印象中的中国传统妇女。这个群体让人联想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等词汇,这些词汇却也使得她们形象浑浊。她们是生活的配角,往往也是文学的配角。现当代中文作品中闪闪发光的女性,多是鲜活多汁、泼辣生风、敢于冒犯禁忌的。而我想写的“中国传统妇女”,并非所谓典型形象,而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多年来,一位老太太在我脑海中婆娑走动,挥之不散。那是我的奶奶,浙江象山人,执拗、敏感、心地柔软。除此,我对她的个人际遇,几乎一无所知。那时我太年轻,没能怀着体恤之心去爱她。我虚构了宋没用,部分出于对她的缅怀。
《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日瓦戈医生》,都是以小人物来命名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式宏大作品,很少以个人来命名。如果有,也多是大人物,如张居正和李自成。这样的作品也书写人,书写苦难,但个体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人类灵魂最深处的秘密,往往是暧昧不清的。
宋没用不是观念的传声筒,她拥有自己的体验、智识,和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写作是艰难的。我满怀问题意识,却又必须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像尊重一个真正的生命那样,尊重笔下的人物。像重视一切工作本身的逻辑那样,重视文学的逻辑。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不过是一根提引着我的隐形之线,让我不致于迷失在中途。
也正因如此,我费时费力最多的,还是文本层面的工作。经过十多年跋涉,我试图回到明清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寻找一种口语式的古典意味。在影视与图像盛行的年代,小说更应有“回到语言本身”的自觉。这是一种差异化策略,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坚持。
在语言往回走的同时,我希望自己在人性图景的层面向前走。写作《好人宋没用》的另一个动机,是向福楼拜的传统致敬。他的《一颗单纯的心》,是我最喜爱的中篇之一。我每年都重读,每次都被小说中的文盲村妇费莉西泰打动。高尔基说:“为何我熟悉的简单的话,放到描写一个厨娘‘乏味’一生的小说里去,就这样使我激动?这里隐藏着不可思议的魔术。”这是对小说家的至高赞美,也是《一颗单纯的心》反复激动我的原因。
其中有技巧的力量,但不仅仅是。费莉西泰的故事,是一个用爱抵抗苦难的故事。直至很久以后,我才能真正读懂,为何福楼拜将这位普通农村老太太鸡零狗碎的一生,与圣徒(《朱利安传奇》)、圣人(《希罗底亚》)的经历并称为《三故事》。我把我的理解,织埋在宋没用的故事里。愿您能够喜欢。
文汇记者:许旸
编辑制作:许旸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