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年6月,某日晚,夜深。维经斯基拧亮桌灯,摊开信笺,书信函告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
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后,工作的进展只限于巩固联系和完成我所拟定的计划。现在我们事实上和所有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有了联系。
维经斯基是于1920年4月间,借居霞飞路716号。其公开身份为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一个俄国人便常外出“采访”,四处活动。不会说中文,旅俄华人杨明斋任翻译,伴随左右。
维经斯基,本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名查尔金。1893年4月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一个木材场管理员家庭。1907年,14岁的维经斯基从市立四年制学校毕业,在维切布斯克印刷厂当了三年排字工人,以后又在白斯托鲁克当了三年会计;20岁那年,移居美国,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在美国的五年,练就一口流利英语。1918年春,回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俄国国内战争期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事工人苏维埃工作。高尔察克叛乱期间,参加反对高尔察克鄂木斯克暴动。1919年5月,遭叛匪拘捕,被判无期徒刑下狱,后流放至库页岛劳役。在此期间,他联手岛上的政治犯暴动,终获自由。1920年1月,维经斯基回到海参崴,开始从事共产国际工作,负责远东事务。1920年4月,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维经斯基第一次出使中国。“他不会汉语,被选拔为赴华使者,大概是因为在北美的生活使他掌握了英语,培养了他的政治感觉”。
布尔什维克身份和革命生涯,令其化名诸多,在史料或教科书里,记有:魏经斯基、维京斯基、维经斯基、威金斯基、威经斯基、吴廷斯基、魏丁斯基、维丁斯基、乌金斯克、沃伊琴斯基、伟基斯克、符定斯克、费丁斯克、胡定斯基、胡定康、伍廷康、吴廷康等。中国人一般称他“维经斯基”,并确认其中国姓名“吴廷康”。
维经斯基的随行人员有翻译杨明斋,俄共(布)党员,亲历十月革命;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及其夫人马迈耶娃等。后来,俄共(布)远东局负责人之一的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米诺尔),也来到中国并与维经斯基取得联系。
信函发往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中共一大代表及其他一些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把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的身份看作是共产国际派来的秘密使者。董必武回忆:“‘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威辛斯基,以后又派三个人来到北京。”
时年,维经斯基27岁。
隔壁人家打麻将,和牌声传来,稀里哗啦。维经斯基习以为常。也是一种很好的掩护。和牌声断续,间隔之间,三至五分钟的静默。维经斯基推算,一副中国麻将和牌,短仅三分钟,长不过五分钟。维经斯基有排字和会计的工作经历,让其行事严谨,长于算计。他来到中国后,先至北京,与人交流,曾被以为其是“学经济统计”出身的,因为他“对苏俄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数字记得很清楚,谈话时列出数字说明革命胜利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
维经斯基继续写信——
……现在我们主要致力于将分散的各个革命小组统一到一个中心上来。“群益书局”可以成为团结这些小组的核心。中国革命运动的最薄弱方面就是行动的分散性。以协调和集中为目的正在开始准备召开全华北(原文如此)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大会。
维经斯基至环龙路渔阳里2号,面晤陈独秀;然后,陈独秀召来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刘太白、沈仲九、丁宝林(女)等人,多次与维经斯基座谈。聚会地点多在陈独秀寓所,即《新青年》编辑部;也去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社。
从在霞飞路716号居所步行过去,几分钟的行程。百年前的上海街景;与日前维经斯基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多有异样。1920年,春天的北京。春光与市声交响,热烈而喧哗。如李大钊所述之北京前门:“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把念世纪的东西,同十五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新的嫌旧的妨阻,旧的嫌新的危险。”中国现代文化熔炉的写照,同时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的乱象。而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环龙路、莫利爱路,繁华与嘈杂。着长衫马褂人等里,夹杂西服革履;俄人法人穿行其间。方圆几里,也与李大钊之语不谋而合——“新旧思想之激战”。
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等讨论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革命问题。维经斯基条理清晰,思路敏捷。他着重介绍俄国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令会者大开眼界,耳目一新。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回忆道:“一九二〇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地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内开会,到会的人数包括国际代表威丁斯基(译名吴廷康)在内,约七八人。”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讲述:1920年夏,他在日本留学放假时,回到上海,在陈独秀家中遇到维经斯基与多人谈话。此情形令周佛海记忆深刻——维经斯基在讨论会上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维经斯基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李达记述:“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很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信函中提及“群益书局”,与《新青年》有关,也与维经斯基注重理论宣传有关。他创办华俄通讯社,这是一个进行理论宣传的机构,包惠僧回忆,“华俄通讯社是维经斯基到中国来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门,由杨明斋负责”。事实上,维经斯基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全部工作的‘灵魂和组织者’”。
维经斯基之函:
一位当地很有名望的教授(陈独秀)正在给各地革命者发信函,以确定大会讨论的课题以及大会召开的地点、时间。大会有可能于7月初召开,我们将不仅参加准备工作(制定议程及决议),而且参加会议。
在维经斯基来华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俄国之间的交通闭塞,北洋政府对来自苏维埃俄国的信息实行严密控制,这使中国革命人士很难搜集到关于俄国革命的信息。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即便是“当地很有名望的教授”陈独秀,无精通俄语的人才,仅利用英语文献资料,从美国共产党的相关信息中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零星启蒙,“布尔什维克主义”,便是由美国而来,对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陈独秀还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曾主张“我们不情愿阶级斗争的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斗争”。陈独秀主张通过“劝说”资本家“采用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
维经斯基带来大量的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由此,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原本来自日本、美国文献的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逐步引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维经斯基协助陈独秀,将同年5月以来便处于停刊状况的《新青年》复刊,复刊号开辟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杂志内容的变化,引原来成员不满,胡适便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其时的陈独秀,在思想上明显变化,1920年9月1日的《新青年》第8卷第l号中,陈独秀著文《谈政治》,承认“列宁的劳动专政”,主张用“阶级战争”和“法治法律的强权”去打破资产阶级旧的政治体制,他还对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还未形成政治实体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
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者维经斯基,起到划时代的作用。
梅雨过后,上海入夏。闷热潮湿。1920年8月17日,深夜。维经斯基伏案,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发函:
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主要工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然后借助于局代表会议把工作集中起来。目前还只建了一个北京局,该局在按照我的指示与米诺尔同志和柏烈伟教授合作。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
信中所谓“革命局”,即是建立于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从1920年5月以来,维经斯基在华期间的主要活动有:以上海“革命局”为建党活动中心;维经斯基还谈到“最近工作的展望”,便是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局”的组织处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外围团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维经斯基“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以此对学生运动施加积极影响,“并引导他们到工人和士兵中间去做有效革命工作”。
维经斯基恢复及开办《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伙友》等书刊;成立上海机器工会;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外国语学社等。
1920年9月创办的外国语学社,由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教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夫人)教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如今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尚存有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在外国语学社教授俄语的照片。
外国语学社还选派数十名学生分批赴俄留学,学社“从成立到结束,历时10个月,为培养党的干部和造就革命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俄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规定和确立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制度、组织形式和组织路线。维经斯基很快得到共产国际二大的信息。他急需得到更多确切的共产国际指示。
维经斯基函告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 处:
关于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的材料以及关于苏俄经济、文化建设情况的专门书籍也是需要的。
1920年8月,陈独秀致张申府,就党的名称问题征求他和李大钊的意见。张申府后来曾两次在回忆中提及此事,一次说:“陈独秀于1920年8月间还来信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没有定。后来,威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另一次说:“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中国共产党的定名,显然受到共产国际和维经斯基的影响。维经斯基这样做,正是通过其在上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得到有关的指示精神,依据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明确规定,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出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16号,往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寓所去。徒步几分钟的行程。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拜访孙中山。1917年的十月革命,同样吸引孙中山的目光。此次与维经斯基会晤,令孙中山直接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也为几年后的国共合作留下伏笔。
那是1920年11月。
时光进入1921年,年初,维经斯基准备启程返俄,离开上海,离开霞飞路。他始终惦念在上海的工作。途经北京,面晤中国同志;张国焘回忆,维经斯基“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一个使者,完成了他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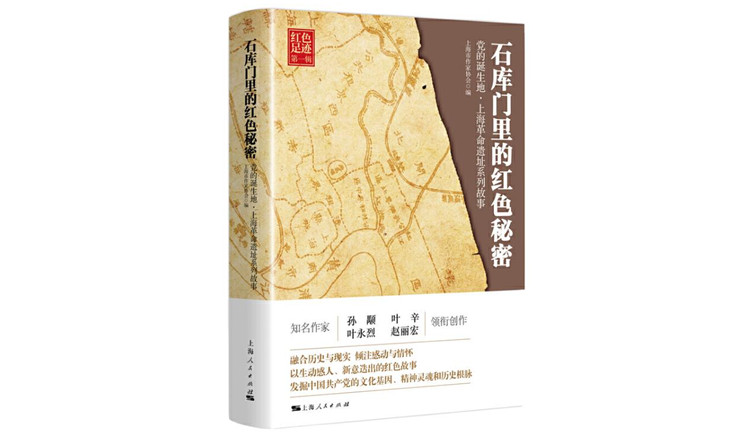
作者:程小莹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邵岭
*本文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