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后失去丈夫和儿女,老无所依的妇人变成了一只狼,“雕像一样低着头,左右打量,然后抬头看向亲眷所在的方向,直到自己完全被对岸的阴影吞没。”
这是托卡尔丘克的短篇小说《怪诞故事集》里一个故事的结尾,继《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和《云游》之后,托卡尔丘克的作品中译本出到第四本。《时间》和《房子》是作家早年的成名作,《云游》英译本获得布克奖,为她在英语世界确立声誉,她的不同阶段不同题材的写作中,延续着一种顽固的精神追求,在最近的《怪诞故事集》,读者能直观地体会到她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强调的:文学察觉到这世界不对头的痛苦,它揭示着人们难以用其它方式向他人展开的体验,在作家的头脑里,微小的碎片顽强地粘合成另一个完整的宇宙。

托卡尔丘克被授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波兰国内的回应是全然对立的两种声音。一位文学杂志编辑曾总结过托卡尔丘克在波兰本土的读者特征:年轻人,来自西部的城市,渴望多元文化,对本国错综复杂的多民族历史抱有好奇心。这些人认为,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在文学和历史的双重层面撕开了新的想象空间。但在波兰的“老派人”眼里,只有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代表着正统正典,托卡尔丘克是历史和文学的双重叛徒。

托卡尔丘克皈依于波兰文学里离散的、甚至被遗忘的那一脉。她的偶像是布鲁诺·舒尔茨,她曾说:“我崇拜且嫉妒舒尔茨,因为我知道自己永远没法写得像他那样好。”布鲁诺·舒尔茨,一个生前靠教书维生的落魄犹太人,生平细节不可考,在出版《肉桂色铺子》和《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薄薄两册短篇小说集后,他被关入集中营。他幸运地因为绘画才能得到一个纳粹军官的庇护,荒唐的是,那位军官因与同僚不睦,泄私愤处死了对方保护的犹太人,对方为了报复,朝舒尔茨的脑袋连开数枪。一个日后被证实写作天分和成就堪与普鲁斯特比肩的现代作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1942年冬天。在被遗忘的尘埃下,舒尔茨留下文学史版图中异常斑斓的一块,他用写作打开了世俗生活中的神秘领域,丰美的、洋溢着感官吸引力的语言,让微不足道的日常事件打开内核,浮现其中无穷灿烂的远景——这吸引了托卡尔丘克。

和舒尔茨一样,托卡尔丘克来自族群杂居的波兰西南。二战后,波兰作为战胜国收复了东德的故土,代价是把东部领土划入俄罗斯,这意味着波兰全境往西“平移”了,东边的波兰与乌克兰原住民被集体移民。“很多波兰人住了下来,根还在乌克兰,思念故土,整天喝得醉醺醺。有些德国人没有走,和波兰人通婚,号称自己是波兰人。有德国人在风烛残年回来寻根,结果倒在波兰和捷克的分界桩旁……”托卡尔丘克生于一个移民家庭,由一个德国奶妈抚养长大,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对“边界”感到迷惑,她的生活和写作,成了一次次穿越“边界”的云游。波兰文学的翻译大家易立君把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形容成“文学品种边缘的小说”“修辞风格混杂、渗透”“各种文体的杂交”,直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纷至沓来,自由驰骋”“七巧板的拼图形成富有凝聚力的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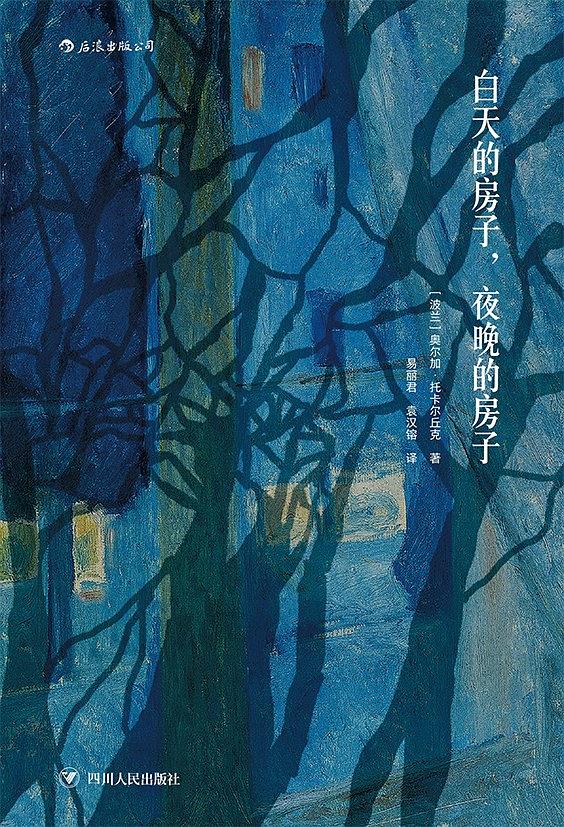
正如舒尔茨相信“艺术家应毕生致力于诠释那些如邮票般贴在他们脑海中的意象”“他们创造性的努力变为永无止境的注解”,作为精神层面的继承人,托卡尔丘克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里借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口吻写下:我不善于再现一个故事本身,但总能再现场面、环境和那个故事在我心中生根的世界……留给我的是故事里某些模糊不清的刺激情节或亮点,我把整个故事忘于脑后,记住的都是些无太大价值的果核和种籽,而后我的记忆由不得不将它们吐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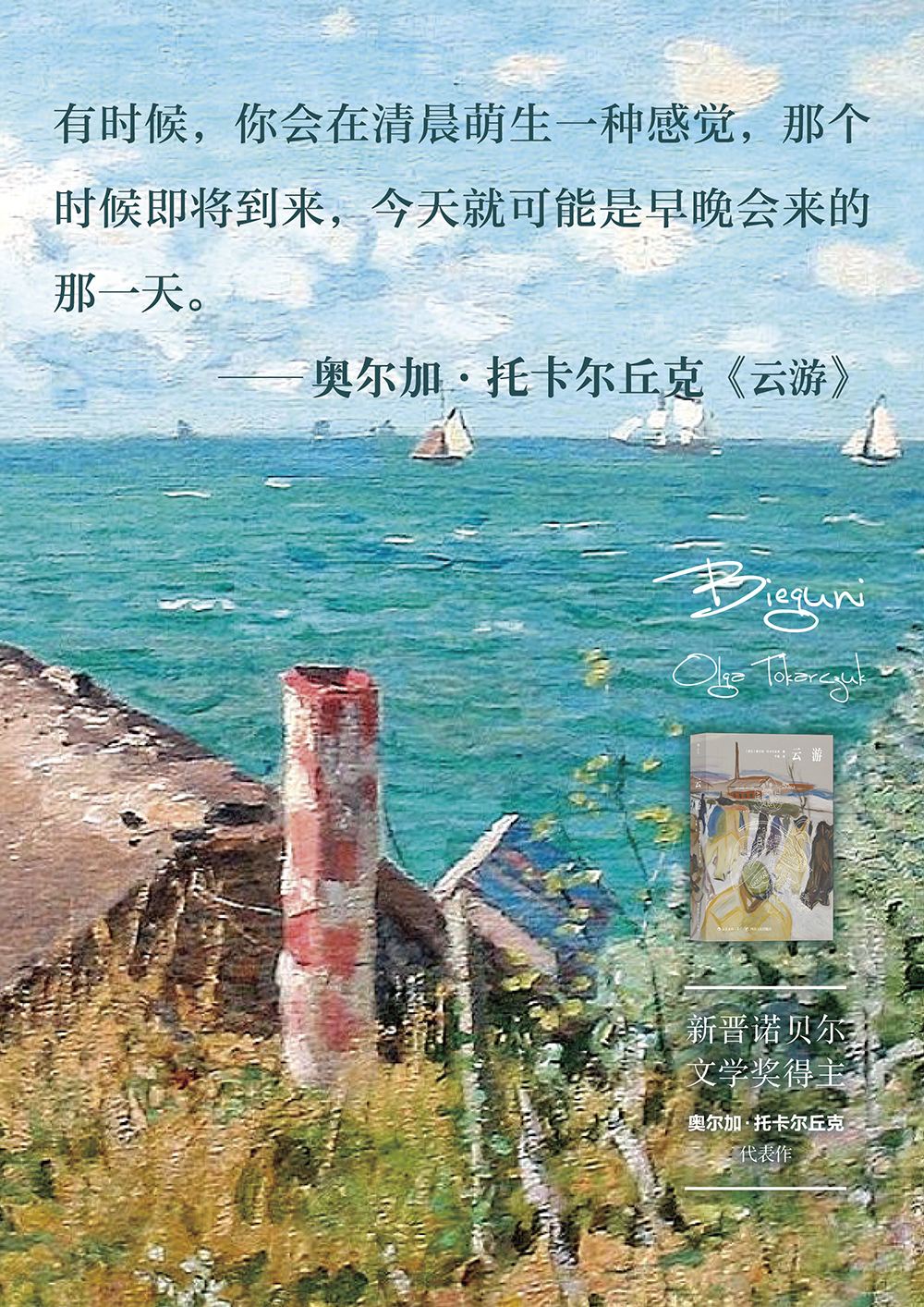
托卡尔丘克在大学里主修心理学,毕业后她意识到“自己比大多数病人还神经质,以至于无法从事这个行业”。从大学毕业到成为专职作家的几年里,她短暂地旅居伦敦,为了谋生做过豪华酒店的保洁员,因此看到了金碧辉煌的走廊两侧,“门背后混乱不堪的房间和那些客人同样混乱的内心”。心理学的科班训练和伦敦生活经历让她面对空白的稿纸时,相信生命的真相是无序且多义的,过于平滑的第一人称叙事难以解码四面八方的杂音。“我写小说,让所有属于人类和超越人类的一切穿透我,把每一件事人格化、个性化”“时间没有尽头,没有以前,没有以后,我不会认识任何新的事物,也不会忘记我见到的一切”,托卡尔丘克的写作创造了新的文体,新的阅读经验,她给小说制造了核裂变的反应。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这些小说里,把作者视为“东欧乡村的民俗守望者”将是一种误读,确切说,她重建了遗失已久的寓言传统,一种甚至让文学编辑措手不及的新的神话——当她把《云游》的定稿交给出版社时,编辑读完后给她发了封邮件:“请问您是不是搞乱了章节之间的顺序?”

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是这样的重要,迷人,原因就在这里:她的写作不是对经验的复刻,她在写作中创造了经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里有一个封圣不成功的修女,祈求上帝把她变成男子的形貌,而写下她的故事的修道士,是个美貌的男孩,同样怀揣着难言的心事。在那个故事里,性别界限是模糊的。《糜骨之壤》里,作家塑造了一个文学史中罕见的愤怒的老妇人的形象,她被村民视为疯癫,捍卫着一个属于狐狸、兔子和鹿的沉默世界,在这里,物种界限是模糊的。直到《变形中心》,万念俱灰的老妇人变成孤狼,消失在阴影里。托卡尔丘克在演讲中提过安徒生童话里一则“被扔在垃圾堆里的茶壶”,她说她在写作中追求的,也是那个沉默的、破损的,“茶壶的世界”。“为沉默者发声”,这份写作者的温柔,不是迎合意识形态正确的口号,而是在喧哗骚动的世界中找到新的故事。

恰如《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麦穗儿的时间》里那段让人心碎的温柔的尾声,麦穗儿被侮辱,被伤害,她在一无所有的时刻,在孩子的坟墓边——
“她看到一个硕大无朋的野兽,一个巨人,她周围的一切是一个大躯干,她的身体是这躯干的一部分。她看到一种渗透万物的力量,她理解这股力量。她看到铺陈在我们世界上下和其他世界其他时代的轮廓。她看到许多无法化成语言的东西。”
作者:柳青
编辑:汪荔诚
责任编辑:范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