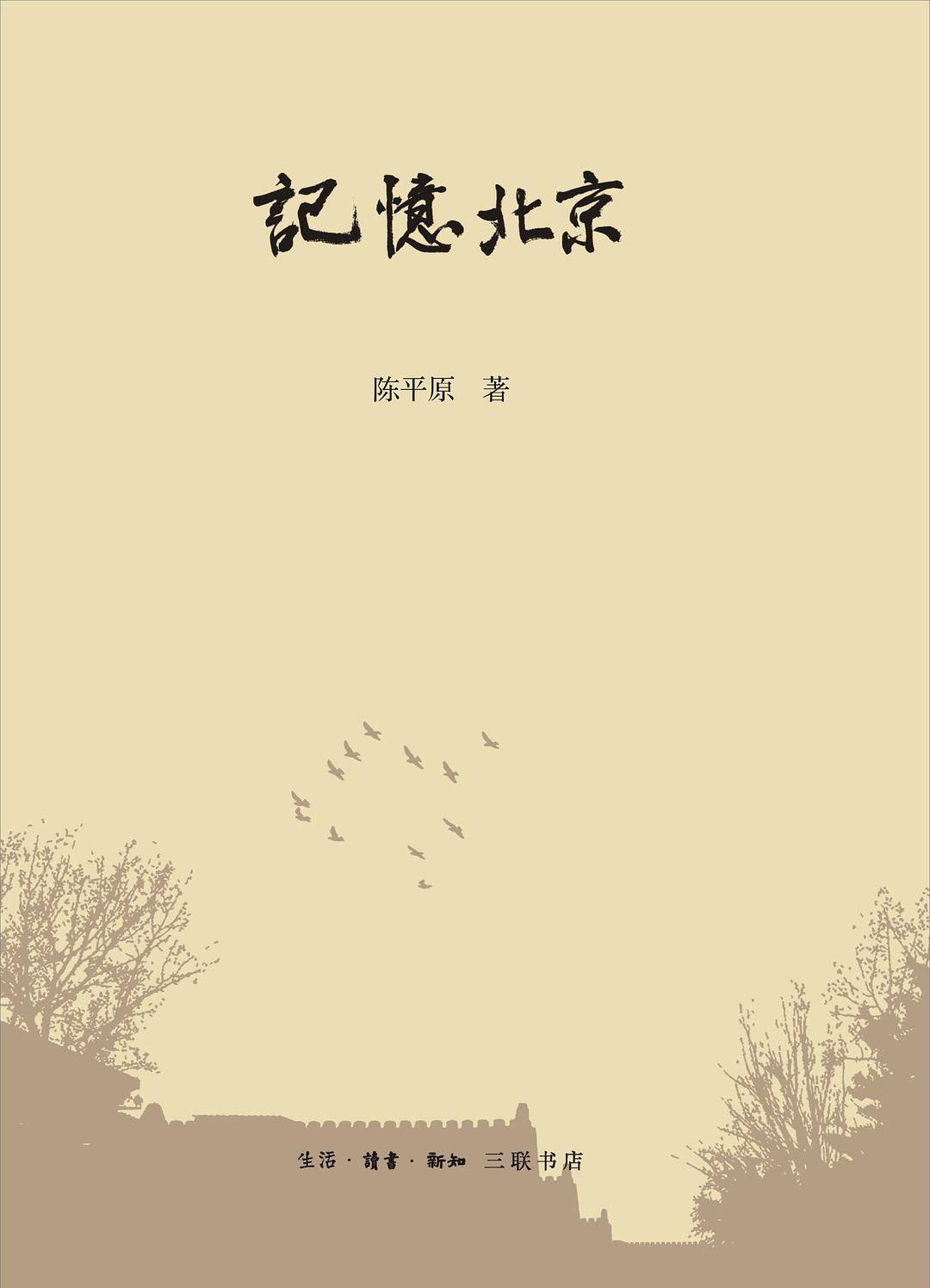
《记忆北京》
陈平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对于身处学术“高阶”、已然“著作等身”的陈平原先生来说,出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他经常是一年之内数本齐发,令读者惊喜连连;而使自己的学术研究长年保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准,不断有新的发想或创见,成为学术界引述或乐道的话题,足见陈先生功力的非凡和学养的精深了。
通常我在见到陈先生的新作时,会比较关注他选篇的思路,看他如何在不断拓展的学术领域内“闪转腾挪”,把旧题翻出新意,或者通过含义丰富的文字体会“压在纸背上的心情”。
摆在面前的《记忆北京》便是一个可以细细品味这几个特点的极好例子。
此书的主角是北京,是透过一个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的学者的眼光窥见的北京,汇集了陈先生多年来关于北京这个大题目所作的深层思考,共计25篇,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陈先生的读博经历、学术研究、教学生涯都是以北京——这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都市为背景而展开的,因此书中关于北京的种种“记忆”,既是学术、教学的具体依托,同时也是阅历与心境的真实记录,体现出的是作为教授、学者的陈平原的“人间情怀”与“谦退不伐”的学术品格。
陈平原是最早提出“北京学”这一课题的学者(见《“北京学”》,《北京日报》1994年9月16日)。从学术的角度而言,以陈先生的资历,自然是做“北京学”的最佳人选,但他倾力更多的是对于学生们的提携,他的助推之力从他这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可见一斑:
2001年秋开始在北大为研究生开设“北京文化研究”“现代都市与现代文学”等专题课,共组织了四轮课程,指导十位博士研究生;在北京、西安、香港、开封、天津等地主持五场大型学术会议;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读本》,为台湾《联合文学》杂志主持“北京专号”,编印《北京研究书目》……
除了课堂上的“言传”,陈先生还非常注重“身教”,他会借春游的名义带领学生游北京,“用脚、用眼、用鼻子和舌头,感觉一座城市”,而站在前门箭楼上对着镜头侃侃而谈北京的历史文化,更是陈先生乐意为之的教学方式。

▲北京城墙(资料图片)
陈先生曾经十分动情地说:
“保不住城墙,保不住四合院,那就保住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这也是一种功德。除了建筑的城市,还有一个城市同样值得守护——那就是用文字构建的、带有想象成分的北京。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学者们用教育、学术、传媒甚至口头讲演等,尽可能让大家留住这个城市的身影,留住‘城与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
“除了呼吁,我们还能做什么?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即使已经成为碎片,也要努力将其连缀成文。”
而对于始终关注的学术研究,他自承:“学生一旦上手,赶紧撤离;若干年后,发现仍‘题有剩义’,那时再杀个回马枪,或者转战到别的领域。”《北京记忆》中的不少篇章就是对“题有剩义”所作的精彩演绎。
虽说目前尚未实现“倚着长城讲唐诗”的理想,但为学术增添温度却已变成陈平原日常研究或教学的习惯。例如他在北大主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从会场的背景和看板的布置就可以看出他对细节的“讲究”,他选择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两张老照片:西直门与景山下的骆驼。对此,他的解释是:“单有高耸的城墙还不够,配上那颇为沧桑的塞外骆驼,北京的味道这才无可置疑。”此外, 他还选用了民国年间大画家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中的水墨人物,作为会议议程表及论文提要的封面与封底。这样别具一格的精巧“设计”深受与会者好评,并成为大家会后争相索要的“纪念品”,这也是陈先生引以为豪的创意。
既经营专业著作,也面对普通读者,能上能下,左右开弓,这是陈平原眼中人文学者比较理想的状态,也是他自己运用得非常纯熟的两副笔墨。
陈平原是个“文、学兼修”的教授,注重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的结盟,喜欢在“学”与“文”之间自由游走。他的学术文章属于好读又耐看的类型,行文时很注重节奏的张弛有致,让气韵在字里行间流转。不少文章的标题一看就很吸引人,像“文学的四季:春夏秋冬”“长向文人供炒栗”“十年一觉”“萧瑟昌平路”等,马上就会把读者带入一个文学的意境。
陈先生能把学问做得如此“有声有色”,与他自觉的语言追求有关。
通常来说,对于学者,大家关注更多的是他在学术上的造诣,思想、见解的新颖独到以及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意义和影响,不太会专门提及语言。其实语言的老到与筋道同样是一部学术作品产生长久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所映照出的是作者全部的学识、修养和文化追求。
陈平原的文章之所以能牢牢“吸”住读者,读着有一种既沉着又痛快的感觉,掩卷后仍令人深思与回味,便跟他在语言上的高度自觉,讲究语言的“粘着度”大有关联。这也是他的学术著作一直拥有忠实的读者群的一个原因。
陈平原喜欢追究作者压在纸背的思考,这和他自己的学术风格比较一致。他的态度也相当明确:
“对于训练有素的学者来说,说出来的,属于公众;压在纸背的,更具个人色彩。后者‘不着一字’,可决定整篇文章的境界,故称其‘尽得风流’,一点也不为过。”
这样的心情与思考在他的论文或专著中可以略窥一二。
比如,写于1990年的武侠文学类型研究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这本书在陈平原的写作经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是一贯谦虚的陈平原自评较高的一部书:“要说写作时精神饱满,思路流畅,中间基本上没打嗝,可称得上一气呵成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庶几近之。”正是由于凭借这一工作,使他重新感觉了生活的意义,也重新理解了学者的使命:“希望学问与人生合一者,往往借著述丰富人生,甚至将其作为危急时刻自我拯救的有效手段”;
再如,在题为《岂止诗句记飘蓬》的论文(2014)中,陈先生对于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写于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进行了深入独到的分析与解读,“读出”了隐藏在诗作背后的心情,把教授们在那个特定岁月咏怀、寄赠、唱和之作,视为中国读书人的心灵史;

▲炒栗子(新华社图片)
而最能代表陈先生对“纸背的温润与深情”寄予的关切的,当属《长向文人供炒栗》一文,它以孤篇压全书之势, 为“北京记忆”作了最为生动有力的注脚。
陈先生从“炒栗”—— 这一北京秋冬时节最为常见的饮食入手,娓娓道来,层层推进:从苏辙的生食栗子治疗“腰脚病”说到陆游晚年时对“火煨栗子”的忆念,再缓缓引出给南宋使臣递送炒栗后“挥涕而去”的李和儿的凄婉故事;接着又借乾嘉年间诗人、学者赵翼、郝懿行对“汴京李和炒栗”的记载进一步强化主题、烘托气氛,铺垫充分后便“自然地”接入周作人称颂郝懿行文章境界的段落,从而点出周作人自身“知”与“行”的矛盾,于是一句“伤心最是李和儿”也便成了对灵魂的拷问。经过这样一番抉微发隐的功夫,笔力已抵达纸背,思想也已触及人性的幽微,但作者并未就此止步,他把笔锋轻轻一转,让“炒栗”从略显沉重的“文学的餐桌”走下,回归生活的日常,以“桂花栗子重糖炒”这样色、香、味满溢的街头情景束尾,从而为文章增添了可触可感的温度。学问做到了这一步,已是令人叹赏的高手境界, 只能用“不凡”二字来形容了。
作者:钟振奋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