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50年,乔治·瓦萨里出版《大艺术家传》,首次提出“文艺复兴”一词。书中记载了一则数学与艺术的趣闻。教皇派特使前往佛罗伦萨,想了解画家乔托·迪·邦多纳(后世称其为“欧洲绘画之父”)是否名副其实。特使索要一幅画送给教皇,只见乔托拿出一张纸、一支蘸着红色颜料的笔,将手臂紧贴在身旁,随即转了一圈,在纸上画出一个相当完美的圆,即便用圆规作画也不过如此。特使以为被戏弄,教皇看罢却大为赏识。
时至今日,以“数学与艺术”为主题的著作已不少见,其意图通常是单边的,即发掘数学中的艺术性或艺术中的数学性,这使我们看到瑰丽别样的图像,比如莫比乌斯带上的蚂蚁以及埃舍尔的无限楼梯等。蔡天新的《数学与艺术》则别出心裁地展示了一种双边的视角:“从数学与艺术的发展历程来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本质属性”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搭建了相对翔实的历史细节、人物生平、背景知识等,还原数学与艺术发展两大主线在所谓“隐秘深处”的交织与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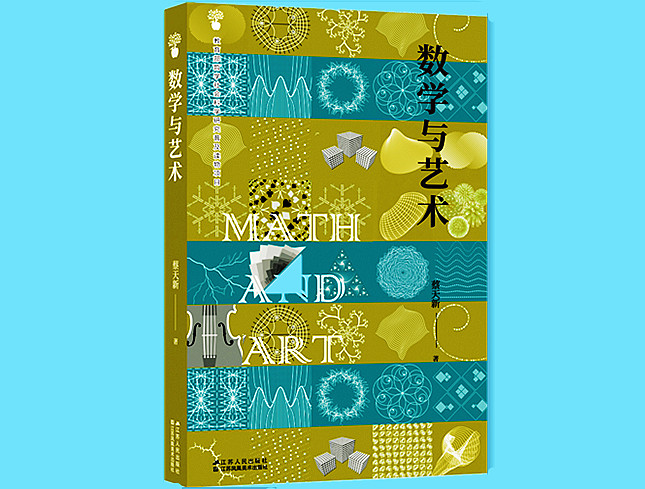
▲《数学与艺术》蔡天新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数学的对象很多是艺术内容
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建立了艺术的准则:艺术的本性就是模仿。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对数学拥有广泛兴趣,其重要原因是“艺术家要创作逼真的作品,除了颜色、形态和意图,他或她所面对的对象本身是有一定空间的几何形体”(第92页),或者说,艺术的对象就是一定的数学内容。上例中,乔托之圆是数学的,同时也是艺术的,因为它由画家绘制,供他人感知、欣赏。
数学的对象包含着许多艺术内容。毕达哥拉斯发现,满足特定数学关系的音程是和谐的,因此提出“万物皆数”的命题;具有黄金分割比的造型,能给人带来奇特的美的享受;数论的研究,发现了完美数、友好数、佩尔方程、费尔马定理等,揭示了自然数本身之美的结果;还有本书封皮上印着的分形的几何结构,形成众多具有特别现代感、精美奇妙的艺术图案。这其中,数学与音乐的关系值得大书特书,这也是本书主题之一。就像大数学家欧拉对音乐理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开创了数学新领域——图论的研究。
数学与艺术发展的“互模拟”关系
逻辑学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叫“互模拟”。以互模拟的概念看,作者在整本书中进行了一场左右互搏的游戏,一人分饰两角,同时饰演支持者与反对者。
从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这一共同的起点开始,艺术发展上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数学史上就能找到欧几里得的《原本》与之相对,其相似处在于以相似的方式各自建立起艺术与数学的准则。到文艺复兴时期,有造型艺术与几何学同音共律。在德国中部的哈茨山附近,诞生了“数学王子”高斯,也诞生了“音乐家中的数学家”巴赫。19世纪,数学上非欧几何的研究打破经典欧式几何的垄断地位,揭示了并非哪一种几何学唯一准确地描绘了现实世界;而艺术上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等流派开始了新的实践,绘画不再是准确地模仿现实,一张画布上可同时容纳画家感受到的、思考到的和想象到的。
20世纪以来,在数学与艺术的重要分支和流派中,数学上有体现个性的拓扑学,艺术上就有载歌载舞、个性鲜明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上有体现共性的表现主义,数学上也有表达共性尤其是抽象化的抽象代数在蓬勃发展。
这种从发展进程的视角对互模拟关系的揭示是深刻的,数学之于艺术,艺术之于数学,都不仅仅是一个随手借助的工具而已。
通识教育与学科交叉的重要意义
或许数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是被类似的创造力所驱动,这种创造力赋予数学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美,冠以数学“科学皇后”之誉,也为艺术开拓出源源不断的新的审美领域。数学与艺术的发展箭头还将向前,当作者从本书的游戏中退场,留给读者的是什么?
继续这场游戏,还是开启新游戏的机会?继续游戏的意义同样是双向的。数学研究者或艺术创作者在追寻新的创造力时,相互借鉴或能相互启发。而开启新游戏,意味着要更广泛地思考在不同学科分科之间内在的关联。不仅在数学与艺术中间没有刻板印象里“理性”与“感性”的楚河汉界,许多虚妄的壁垒都阻挠着更深的认识。这也让我们更能理解当前教育界提倡通识教育与学科交叉的重要意义。
作者:魏 宇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