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尼(Karen Horney,1885-1952),德国出生的美国女精神分析学家。她的重要著作包括《精神分析的新方法》《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又译《自我的挣扎》),以及她去世后被整理出版的《女性心理学》等。在《自我分析》一书中,霍尼博士讨论了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以及个人通过使用心理分析技巧可以多大程度解决自己的问题。她谈到了神经症中各种驱力、心理分析的各个阶段患者和心理分析师分享的经验、随机的也有系统性的自我分析,以及对实际操作自我分析的可能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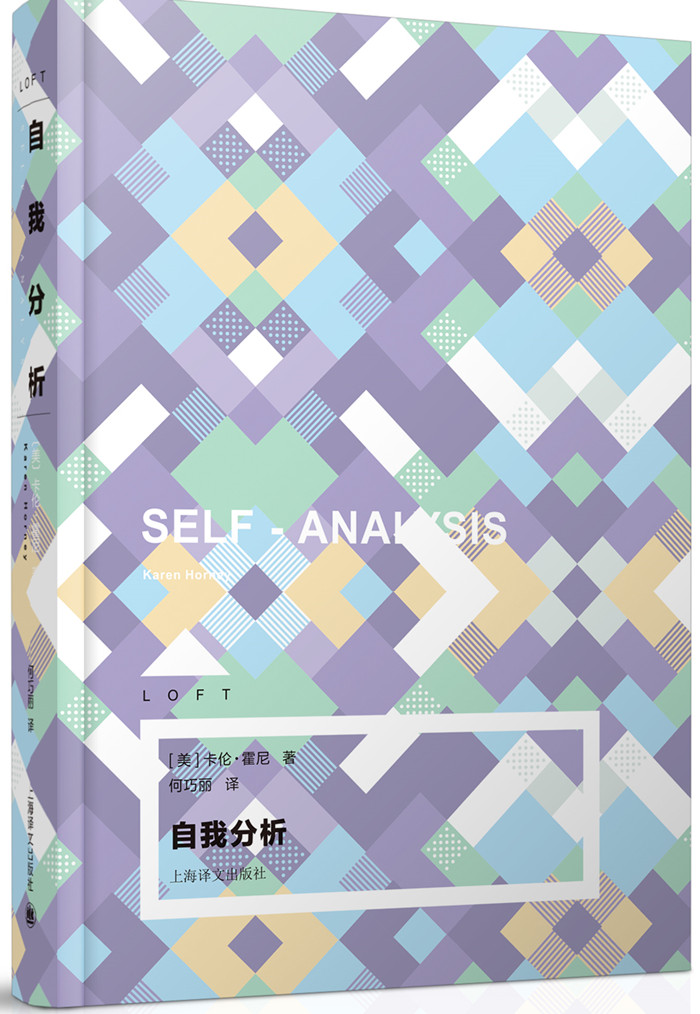
《自我分析》
[美]卡伦·霍尼 著
何巧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相关阅读
每一个分析师都知道,病人越“合作”,分析的过程就会越快、越有效。说到“合作”,我脑海里想到的不是病人出于礼貌或者体贴而接受分析师给出的任何建议;也不全指病人在意识中情愿提供关于自己的信息——大多数出于自愿来接受分析的病人迟早都会认识到并且同意: 尽最大可能真诚地表达他们自己。我更多地是指这样一种自我表达: 它很少听命于病人有意识的命令,就像作曲家很少能够有意识地命令自己用音乐表达感受一样。如果在内心有一些因素阻碍了他去表达,那么作曲家必将无法创作,他将徒劳而无所出。同样地,一位病人,不管他有着多么良好的合作愿望,一旦遭遇“阻抗”,也将徒劳而无所出。因此,他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时候越多,他就越能处理自己的问题,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共同的工作也越有意义。
我经常告诉我的病人们,理想的情况是,分析师只扮演向导的角色,在攀登一座难以征服的山峰的旅途中,告诉病人走哪条路会有收获而哪条路最好不要走。更准确一点,还应该再补充道: 分析师这个向导自己对走哪条路也不是非常确定,因为尽管他有爬山的经验,但是他还从没有爬过特定的这座山。这种情况会使得病人的心理活动和产出能力更加令人满意。几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除了分析师的能力之外,病人的创造性活动决定了分析的长度和结果。
常常是在病人的状况仍然不佳,而分析过程却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打断或者终止的情况下,分析性治疗中病人心理活动的重要性才被揭示出来。病人和分析师都对取得的进展不满意,时间流逝,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分析;但是之后某一时刻,他们可能发现自己收获了意外的惊喜: 病人获得了重大且持久的改善。如果仔细审视后没有发现他的生活环境有什么变化可以解释这一改善,那么就有理由相信这是迟来的分析效果。当然,这种滞后效应不容易解释,可能与各种各样的因素有关。可能之前的分析工作让病人有能力准确地观察自我,因而比之前更加确信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令他烦恼的倾向,或者他甚至能够发现自己内里存在的影响因素。或许也可能是,之前他把分析师的任何建议都看作是外来侵入物,而现在当这些洞察作为他自己的发现再次出现时,他能够更轻易地抓住。又或许,如果他的问题就出在他有一个固执的需要,要去超越别人、打败别人,他可能没办法把分析工作成功的满足感给予分析师,那么只有当分析师淡出视野之外,他才能够好转。最后,还必须注意的是,延迟反应也发生在许多其他情形下: 有时只有在过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领会一个笑话或者一次交流中说过的话的真正含义。
这些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都提示有某些心理活动发生在病人身上,但是病人自己并不知晓,或者至少没有在意识层面下定决心努力探索过。这种心理活动,甚至是有意义导向的活动,的确发生了,我们也的确没有意识到。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会做一些有意义的梦,以及我们有这样的经历: 晚上被某件工作绊住了脚,早上一觉醒来却找到了解决办法。不仅有著名的数学难题在一夜睡醒后答案浮现;还有些决策也是如此: 晚上被困住了,“睡”过去了就清楚了。有时候你心中的憎恨可能白天一点都没有被觉察到,但在睡梦中却非常强烈地突破限制进入我们的意识,以至于我们会在清晨5点钟突然醒来,清楚地感受到被激怒的感觉以及相应的情绪反应。
事实上,每一位分析师都仰赖于这些潜在的心理活动来工作。这种仰赖隐含于这样的信条中: 如果移除了“阻抗”,分析的进程就会令人满意。我想强调的是,这里还存在积极的方面: 病人向往自由的动机越强、障碍越少,就会展现出越多富有成效的活动。但是不管是强调消极的方面(阻抗)还是强调积极的方面(动机),底层的原理是一样的: 移除障碍或者激发足够的动机,病人的心理能量就会开始工作,他就会为临床提供材料,这些材料最终通向一些更深层次的领悟。
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可以向前再多走一步。既然分析师仰赖病人无意识的心理活动,那么如果病人有能力独自向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探索,这种能力可否用一种更精细复杂的方式来使用?病人能否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力和理解力来检查其自我观察结果或者自由联想?一般而言,在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存在一个分工: 病人让自己的想法、情感和冲动浮现出来,而分析师用他的判断力和理解力去发现病人的用意所在。他追问病人陈述内容的正确性,他把看似不相关的材料放在一起,他就可能的意义提出建议。我说“一般而言”,是因为分析师也使用他的直觉,且病人也会将某些事情联系在一起。但是大致上,存在这样的一个分工,且这样的分工对分析过程确实有益。它让病人能够放松,仅仅表达或者记录浮现的东西。
但是两次分析之间的一天或者数天怎么办呢?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分析被打断了,出现了更长时间的停顿,该怎么办呢?为什么期待某个问题会在不经意间自己清晰起来?就没有可能鼓励病人不仅仅去详细准确地观察自己,还能运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得到一些领悟吗?就算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充满了危险和限制——这点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这些困难也不应阻止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个人有没有可能自己去分析自己?
在更广阔的参照框架下来看,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值得尊敬的问题: 一个人能否认识自己?令人鼓舞的是,人们一直认为这项工作尽管困难,却是可行的。然而,这种鼓舞不能带领我们走得更远,因为古人如何看待这项工作与我们如何看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我们知道,由于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这项工作比起古人能够想象的要复杂困难得多——的确,它是如此之难,以至于仅仅是严肃地提起这个问题都像是去未知的地方探险。
作者:[美]卡伦·霍尼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