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游戏——西方现代文学十八讲》收录的文章是作者应文学杂志《花城》之邀,在该刊开设的“世纪经典”专栏发表的系列文论。这些文章贯穿着“批评即创作”的诗学理念,即以中国传统诗学方法与西方现代诗学方法相结合的、宏阔的诗学视野,讨论了包括弗兰茨·卡夫卡、阿尔伯特·加缪、马塞尔·普鲁斯特、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罗兰·巴特、华莱士·史蒂文斯、勒内·里尔克、罗伯特·弗罗斯特、巴勃罗·聂鲁达等人物在内的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
在文体上,一方面,极力倡导对中华传统文论诗性书写方式的回归;另一方面极力倡导诗意书写的诗话文风,以超越学报式的论文写作模式,实践理论与创作并立而会通的书写途径,使艰深的学理变得富有诗意,亲切可读。作者认为,在西方主流学术文体和学术成规独大的今天,创造性地回归《文心雕龙》《人间词话》《驼庵诗话》的文体批评精神,本身就具有推动“中华文艺复兴”的一种书写力量。从本书可以看到,20世纪西方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在著者的诗学批评中已经得到创造性地重读,这种重读恰恰就是一种新的诗学理论的建构;这种批评不是用一种理论去套牢作品的解读方式,而是那种接着大师作品书写的方式,是理论高度与文体之美并肩、精神格局与杰作媲美,以唤醒杰作的艺术生命并创造新的艺术生命的方式。因此,这种批评与创作并肩而立的创造性诗学解读,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值得肯定的新范式,是中国传统诗话与当代理论结合的播扬文化道路自信的有效探索方式,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与创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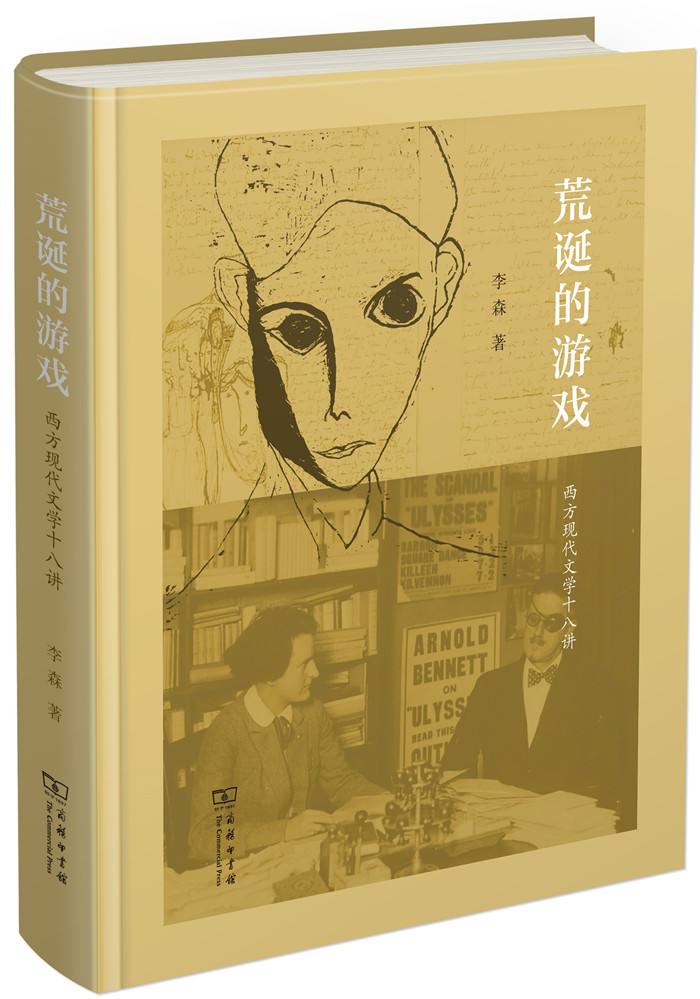
《荒诞的游戏——西方现代文学十八讲》
李 森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读:
上大学期间,我读弗兰茨·卡夫卡,读《变形记》或其他作品,只觉得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到连骨髓都要结冰的程度。他在墓穴中游荡,与鬼魂或魔鬼对话;他亲近棺材,看见鬼魂递给他丧服;他在冰冷的高天之外行走,回首人间,把春秋看透。我还知道,他是现代派文学的开拓者之一,用现代派的手法写作(这是学者们说的)。他在现代西方文学史上很重要,即使读不懂他的作品的人,也不敢说他不重要,而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更是不能不了解这个生在布拉格的波希米亚之子。(杰出诗人里尔克也出生在那里。里尔克生于1875年,长卡夫卡8岁)多年以后,卡夫卡的全集翻译出版了,我系统地阅读卡夫卡的作品。
这个时候,我认为我才真正地理解了卡夫卡。理解卡夫卡的确是需要时间的,一个卡夫卡的读者需要成长,需要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单纯,在成长中回归。卡夫卡的存在十分遥远,一个到达卡夫卡的读者,要像高山上的一棵乔木一样,经过无数次掉光了叶子的洗礼。我到达卡夫卡的时候,好像正好从冰凌推动着的岁月之河中爬上岸来,而多少年前,卡夫卡也是从这条河流中爬上岸的。我不知道谁曾经牵着卡夫卡的手上岸,而我,则很荣幸地被卡夫卡拉了一把,让我到达了高高在上的明亮之处——这亮处,浑浊的水正在退去,清澈的水浪浪涌来。因此,我得以在永不疲倦的风中从高大的、光秃秃的枝头冒出嫩芽。我是梦想中的花和果实,但现在是嫩芽。
卡夫卡有一则箴言:
许多亡者的影子成天舔着冥河的浪潮,因为它是从我们这儿流去的,仍然含有我们的海洋的咸味。这条河流对此恶心不堪,于是翻腾倒流,把死者们冲回到生命中去。但他们却欣喜万分,唱起感恩歌,摸着这愤怒的河。
我有一诗《梦见河水》:
河水在流淌,光在照耀
又有谁在打捞
又有谁
在模仿海鸟
从天边飞来
有人在熊熊的火焰里
打制新的铁锚
有人窗前
照镜子
但还没有人知道
水起源于
泰勒斯的那颗心
那颗心
超越了生和死
无数个宁静的深夜,我在远离混乱的文学江湖竞技场之外,与卡夫卡谈话。(文学江湖的竞技场中,人们正在为利益厮打,只听见污言秽语,只看见刀光剑影。)毫无疑问,我崇拜我心中的大师,他,弗兰茨,伟大得让我喘不过气来。他是淘沙者眼前的一块巨石,是沙的宇宙。最后一滴水已经蒸发,所有的金属都被淘走,而巨石仍旧立于白沙之中。沙中之沙,巨石,曾经穿透云层,穿透空无,落下来;沙中之沙,巨石,曾经破开岩层,穿过沃土,出自黑暗。现在,它是寂静的,他是弗兰茨·卡夫卡,我的兄长。
作者:李 森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