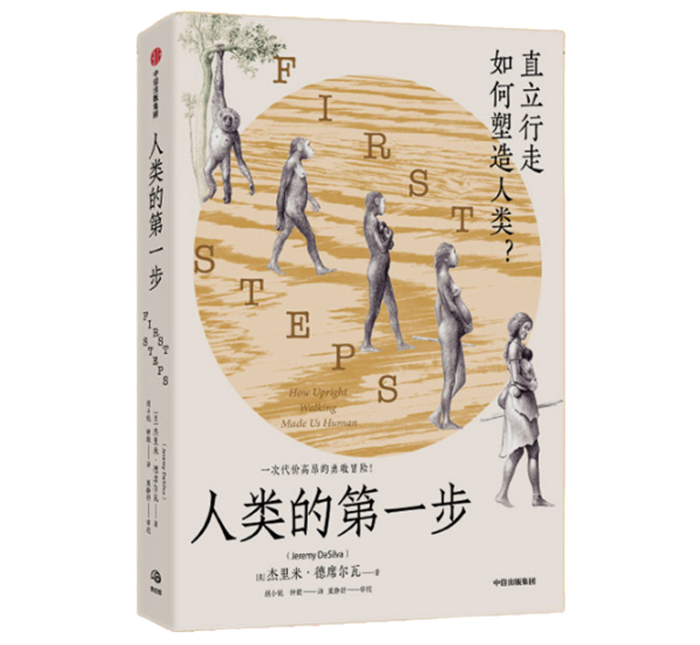
《人类的第一步》
[美] 杰里米·德席尔瓦 著
胡小锐 钟毅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直立着探索这个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本书聚焦人类用双足直立行走的独特能力,探讨它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以及如何塑造了现代人类。
直立行走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有信念、有控制地向前倒。这是一个无比勇敢的选择。它不仅仅是一次解剖结构方面的大变革,更涉及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多方面身心适应,我们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比如:速度变缓,分娩困难,腰椎、膝盖和脚踝变得脆弱。可是,两足行走为人类学会使用石器和火、大脑容量剧增及其他特征铺平了道路,更是促成了人类的社会性、同理心,深远地影响着科技、语言、觅食和育儿方式的发展。
灵巧的手、无毛的身体、硕大的大脑……勇敢选择直立行走,让我们成为人类。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当下的生活:每天一万步,是噱头还是铁律?边散步边思考是天才们的成功秘诀吗?怎样用散步来对抗时间的侵蚀,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直立行走定义了人类,也将继续塑造我们。
>>内文选读:
一个直立行走如何塑造人类的故事
古人类学研究的当然是古人类。这是一门科学,它提出了一些人类之前不敢想的关于人类和世界的最重要、最大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能生存下来?我们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是怎么来的?但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踏入这个领域。在2000年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有这门科学。
那一年,我在波士顿科学博物馆从事科教工作,时薪是11美元。同一年,小布什当选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红袜队连续第82次冲击世界冠军未果。我在博物馆的合作伙伴是一位优秀的科教人员,她的笑声是我听过的最动听、最有感染力的。四年后,她接受了我的求婚。但是在2000年下半年,我心里想的不是爱情,而是博物馆大厅里的一个严重失误。恐龙展览馆里展出了360万年前古人类在坦桑尼亚莱托里留下的脚印的玻璃纤维复制品,它的旁边是实际尺寸的雷克斯暴龙。就像把恐龙、长毛象(真猛犸象)和史前穴居人放到一起做成史前动物玩具套装一样,把这些脚印放在年龄比它们大20倍的恐龙化石旁边,可能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古人类和恐龙共存的误解。
我觉得必须做点儿什么。于是,我找到了我的上司,也就是杰出的科教工作者露西·科什纳,提出应该把古人类脚印模型放进新近重建的人类生物学展馆中。她同意了我的提议,但要求我先去博物馆的图书馆,尽可能多地了解莱托里脚印和人类进化的相关知识。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方面的书,很快我就着迷了。用他们的话说,我染上了古人类病毒——“古人类”就是指已经灭绝的人类近亲和祖先。无巧不成书,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人们发现了人类谱系中最古老的成员——神秘的类猿祖先,包括地猿属、原人属和沙赫人属。

2002年7月,我和劳拉·麦克拉奇博士(当时是波士顿大学的古人类学家)一起站在博物馆的展示台上,和一群着迷的公众讨论在非洲乍得新发现的700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有什么重要意义。和一位真正的古人类学家谈论到那时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这让我异常激动。对我来说,古人类化石不仅是人类进化史的物证,还承载了逝去生命个体的异乎寻常的故事。例如,莱托里脚印是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的一生的快照,属于直立行走、会呼吸、会思考的生命。我想了解科学家是如何从这些古老的骨头中挖掘信息的,我想讲述关于我们祖先的有真凭实据的故事,我想成为一名古人类学家。
在博物馆舞台上与劳拉·麦克拉奇合作后一年多,我进入了她的古人类实验室(当时在波士顿大学,但随后不久就搬到了密歇根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现在,我在新罕布什尔州丛林中的达特茅斯学院人类学系任教,经常远赴非洲从事研究。近20年来,我一直在南非的洞穴和乌干达、肯尼亚古老的不毛之地寻找化石,在坦桑尼亚莱托里的古老火山灰中寻找数百万年前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留下的更多足迹,跟在野生黑猩猩身后探索它们在丛林中的栖息地。我还前往非洲的博物馆,仔细研究已经灭绝的人类近亲和祖先的足部化石。我想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
我想了解我们硕大的大脑、复杂的文化和先进的技术;我想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说话;我想了解为什么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人一起努力,是否一直如此;我想了解为什么分娩如此困难, 有时甚至危及女性的生命;我想了解人类的本性为什么时而善良、时而暴力;但最重要的是,我想了解为什么人类用两条腿而不是四条腿走路。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想了解的许多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而归根结底都与我们不寻常的行走方式有关。两足行走是通向人类许多独特特征的大门,是人类的标志。要理解这些联系, 就需要在问题的驱策下,在立足证据的基础上看待自然界,这是我从6岁起就开始接受的方法——科学。
作者:[美] 杰里米·德席尔瓦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