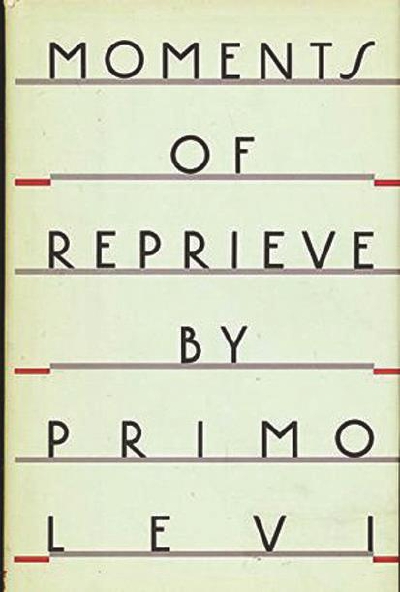
▲普利莫·莱维的《缓刑时刻》
在一个因为加莱亚诺而奔赴图书馆的下午,我在拉美作家隔壁的意大利作家书架上意外地邂逅了普利莫·莱维。从书架上挑出《缓刑时 刻 》(Moments of Reprieve)的那一刻,我并不知道眼前这本薄薄的小书有多沉重、又有多珍贵。
200页不到的小书中共有15个故事,主角都是些在奥斯维辛不太引人注目的小人物:化学实验室里的德国女孩、管理犹太人的原是杂技师的德国男孩、志愿到工资更高又提供住处的集中营地区工作的沉默寡言的意大利石匠……若用宏大的镜头一一扫过这些人,很容易把他们看成纳粹这一巨大的罪恶机器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帮凶的话。或者,用莱维在自序中的说法,便是 “在(人性之)船快沉没时不知姓名、面目模糊且悄无声息的一群人”。
但在这似乎已成共识的定论之外,莱维却拿起了化学家的显微镜照出了他们的面目、捕捉并铭记了他们哪怕转瞬即逝的 “做出反应的意志与能力”。他的显微镜,使每则故事无需延展修饰,便自成一部二战的微观史诗。
最意外的,却是在书中读到了 “犹伪”鲁姆科斯基的故事。在耶路撒冷参观Yad Vashem之前,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纪念馆简单地讲述了他追逐权力却终究难逃毒气室一死的人生悲剧(或者,在任何有关大屠杀的叙述中,“悲剧”这个词都得省着点用,才不至于显得过于廉价?)感谢莱维这本厚重小书的最后一篇,把纪念馆三言两语的平面文字,还原成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
鲁姆科斯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受到了神的眷顾。他早年是当地一座天鹅绒工厂的共同所有者。破产后去了俄国,旋即重新发家。财富被十月革命摧毁得所剩无几后,他又重返罗兹。到隔离区设立前后,年届六旬的他已是当地数个犹太慈善机构的董事。
鲁姆科斯基在罗兹隔离区主席的宝座上坐了四年。他知道隔离区里的艺术家整日食不果腹,便用四分之一块面包诱使这些人设计印发画有他头像的邮票;那些“非法学校”(1940至1941年间,罗兹共有36所小学及9所其他各类学校。但1941年10月后便停止运营。此后的“学校”便为“非法学校”)的孩童们不时受到饥饿与纳粹的死亡威胁,却被布置文章“赞美歌颂敬爱的、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席先生”;直至被送往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鲁姆科斯基坐的都是符合其“尊贵地位”的专属车厢……
可是,那又怎样呢?在终究无法逃脱的死亡面前,坐专属车厢去死,或是像犹太平民那样如沙丁鱼一般挤着货运车厢去死,又能有什么区别呢?
鲁姆科斯基的故事被安排在书的最后,或许不仅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也不仅是因为他直到生命尽头才与这本书所致力回忆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有短暂的交集。因为这个故事就连主题也与之前的所有故事不同。后者是在巨大的泥淖里有意无意迸发出的善良、温暖、慷慨与宽容。鲁姆科斯基的结局,却是被这块权力与罪恶的泥淖所吞噬。
即便如此,莱维却并没有把他描述成纳粹一般的恶魔。尽管他也认为,假使鲁姆科斯基活了下来接受审判,也不会有任何法庭会赦免他;但莱维还是看清了这位不可饶恕之人之所以得此下场的更深层的悲剧:
权力就像毒品,没有尝试过的人无法理解这位或那位上瘾者的需要。但一旦开始尝试,可能只是不经意间,毒瘾便产生了……
如纳粹这般来自地狱的命令,使出的是一种猝不及防的致命的诱惑力……必须具备真正坚强的道德盔甲,才能抗拒(纳粹)的腐蚀性。而罗兹商人鲁姆科斯基,以及当时整整一代人,他们的道德盔甲都是脆弱的……鲁姆科斯基的故事是一个令人叹息和不安的故事。那些会说“就算我不去做,也会有比我更坏的人去做”的人们的故事。
若有某种道德上的洁癖,一定不会认同对罪恶哪怕一星半点的开脱。甚至某种程度上,这本书本身不也是对这种托辞的有力反驳吗?毫无疑问,这本书(乃至莱维的所有作品)的大部分篇章是灰暗压抑的。但书中记录的沧海一粟般微渺的善,却像是灰暗篇章里星星点点的亮色,照亮人类在最深渊处仍未完全泯灭的希望;面对来自苦难风暴正中心的第一手记录,便只剩静静聆听的谦卑。和平年代的道德高地任谁都可以凭口舌轻易地攀爬、占领。只有真正见识过地狱之黑暗的人,才能深刻体会恶魔般的敌人摧枯拉朽的强大,体会到人性在这种残酷的考验时难以避免的脆弱。
由此,当莱维提及那一代人“脆弱的道德盔甲”,我虽不一定认同,却深深地表示理解。我甚至怀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性很有可能一如既往地脆弱着。对这终极拷问只能想象的当代人,真正经受这种考验时,“金刚”之身还有几分能“不变形”,不见得就比前人更有把握。
在悲天悯人地哀叹完人性的脆弱之后,莱维接着写道,鲁姆科斯基的悲剧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再典型不过:
它意在削弱、模糊人们做出判断的能力,在恶魔代言人与纯粹的受害者之间创造出一个“灰色良知”的广阔地带。
在为鲁姆科斯基、乃至这本书里的所有故事流下太多无力的眼泪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在合上书页的那一刻重振精神、稍微乐观一点了。因为读懂了这段话,过往悲剧该如何永久避免的钥匙也就浮出了水面;而那仅存在于想象中的严酷拷问,恰恰是和平年代里最值得珍惜的幸运。(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
文:严奕飞
编辑制作:王秋童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