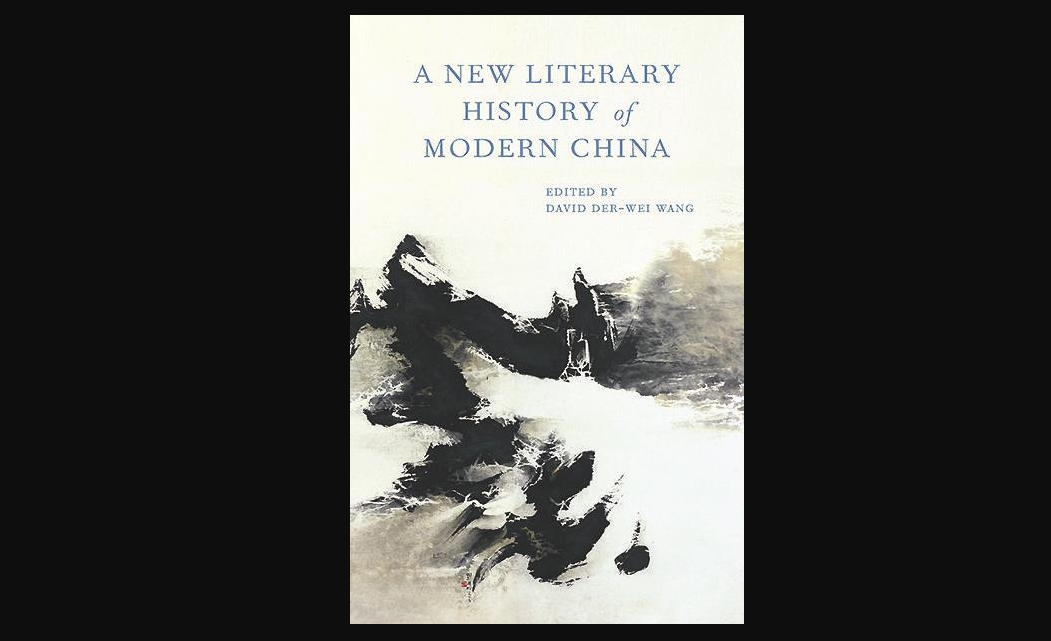
青春不仅对个人成长具有意义,更为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提供历史的新视野。过去一百年间,“青春”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象征符号,在中国知识话语中发挥了主导性修辞作用,并几乎成为一切进步象征词语的核心。
哈佛大学出版社自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推出文学史新编系列,迄今出版法国、德国、美国、中国(现代)四卷。编辑体例在四卷中有统一规定,按照编年次序来撰写,每一个年代,对应一个事件,再在更大意义上对应一个文学史或思想史的主题。例如,本文选择的时间点是1916年9月1日,在这个时间点上,《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李大钊的散文《青春》,而这篇文章的诞生、内涵、影响涉及二十世纪中国的青年文化,有关少年中国的种种论述,以及描写青少年主人公的现代小说基本形式——成长小说。本文选自王德威主编《哈佛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撰写所依据的是作者宋明炜的著作《少年中国:青春话语与成长小说》(英文版:哈佛亚洲中心,2015;中文版:即将出版)。
1916年9月,一篇题为《青春》的散文刊载于《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号,这份由陈独秀(1879—1942)主编的杂志在一年前才开始出版。作者李大钊(1889—1927)在同时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久之后,他与陈独秀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参与编辑《新青年》、并为其勤奋撰稿的李大钊与其他启蒙知识分子,为何能够成为接下来几十年里改造中国并重塑其文化的一股前所未有的新生力量的代言人,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种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他们成功地将他们心目中的时代精神清晰而生动地凝聚在一个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单一文化符号之中,那就是“青春”。李大钊《青春》文白夹杂,词藻生动,意象迷人,他借用许多比喻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青春”——以及这个词语同时指向的青年人——的活力和美好。李大钊强调的是青春所具有的复生之力,由此青春可以用来表达希望和未来;青春不仅对个人成长具有意义,更为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提供历史的新视野。作者召唤中国重获青春之转型,他将青春表述为无所不能的变革的象征,这样的象征性的力量被赋予从自我、家庭、国族一直延伸至整个人类乃至宇宙全体,一切都有青春,一切都可以重获青春。
“青年人”的崛起,是现代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年轻人要尊重长辈,任何试图改变这种等级关系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僭越和冒犯。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出现了一种对青年的崇拜,从此改变了长幼之间的等级秩序,推动社会改造和革命,这个现象对中国现代知识界发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在过去一百年间,“青春”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象征符号,在中国知识话语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修辞作用,并几乎成为一切进步象征词语的核心。在文化的现代性意义上,“青春”代表着新生、未来和改变;它在近代获得一种象征意义,这种意义超越了原来将青春期看作不成熟和脆弱敏感阶段的生物学定义,使之能够应用于整个世界处在无限变化中的现代变革,以及由此对这变革找到反思的契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不安定、难以琢磨、变化多端的青春形象,却成为具有着革命潜能的最具决定性的现代形象,其中既包含除旧布新的力量,又孕育着有关未来理想的愿景。从常变常新、活力永驻的青年形象中,有许多政治、文化和文学想象的新范式开始生长。
对“青春”的现代礼赞,最早是由晚清改革家梁启超(1873—1929)在其石破天惊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的,而梁启超这篇后来脍炙人口的文章,恰好发表于中国进入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农历新年的正月。在文中,梁启超以壮丽的比喻和有力的修辞召唤民族的青春复兴,他意欲将中国的意象从老迈帝国重写为“少年中国”。对于无论是个体、还是民族象征的青年,他赋予之无限美好的愿景:“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体现他的政治愿望,那就是中华帝国可以返老还童,进入富有竞争力的年轻国家的行列,由此登上国际政治舞台。通过命名“少年中国”,梁启超为中国塑造了一个崭新的民族理念,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个理念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它不仅意味着中国在对抗兴盛的西方世界时能够克服挫折,也意味着在世界历史新的时间表上,中国经过浴火重生,重新变成一个年轻的国家。梁启超借鉴的是像意大利和日本这样的新兴国家,少年中国与少年意大利、少年日本,可以一样重生为富强的民族国家。在使用“少年”来命名中国的同时,梁启超笔下的“青春”(晚清时期,青春、少年、青年的含义时有互通)这个词语也获得超越其仅仅作为形容词的意义。他加诸青春的政治象征,使它成为一个普遍的文化符号,意味着“历史进步”的现代视野。青年人的活力,不仅能使民族复兴,也推动一种新的时间概念形成:这是一个永远保持最新、永远保持向前的历史运动,正如李大钊后来所赞美的那样:
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
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来更名为《新青年》),最终为抗衡传统的新一代中国青年赋予了一个集体名称。毫无疑问,吸引当时的年轻人响应“新青年”之理念的,是前所未有的对个体自觉的强调。《青年》杂志第一卷即以陈独秀对年轻读者的热忱“敬告”而开场:“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新青年》后来的各种论述中,将传统描绘为令人窒息的体系,或者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言,是“吃人社会”。对于中国青年来说,更加急迫的使命,就是把自身从传统的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新青年这一代的自我塑造,激发了文学创作中的新形式,文学上的青年书写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达到极致。这类创作聚焦于新青年自我身份的塑造,隐含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个性解放和民族复兴糅合在一起,并被结合在青年参与历史运动之过程的情节中。
一些最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都突出了这样的场景:年轻的主人公以阅读《新青年》作为观念转变、追求新我的开始。在叶绍钧(1894—1988)的《倪焕之》(1928)里,当主人公不断在事业和婚姻生活中遭受挫败而感到自己的理想已经受到侵蚀之际,他从这本“新”杂志中发现启迪,重塑价值观,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在茅盾(1896—1981)的《虹》(1930)里,梅女士在读了《新青年》后,感到自己经受了精神的洗礼,成为一个充满自决意识的新女性。在巴金(1904—2005)的《家》(1931)里,高家兄弟激动地阅读和讨论《新青年》上的文章,甚至于那位被描写为墨守成规、屈服于家长权威的大哥觉新,也感受到自己失去的青春在体内甦醒。
《倪焕之》是中国最早一部整体聚焦于青年心理成长的现代小说,在其开篇,主人公离开他的故乡,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离家远行,去往远方的旅行,向他承诺生命的崭新篇章。虽然他乘坐的小船被黎明前的黑暗所吞没,他仍然感到如同正沐浴着明亮的光芒一般。他幻想着可能发生的所有变化:新生活从此开幕了!出现在中国最早一部涉及中国新一代青年成长经验的长篇现代小说中的这一时刻,具有高度的寓言意义。旅程和梦想,激情与承诺,希望和未来——这些元素构成了中国现代青春叙事的核心情节基础。
《倪焕之》出版于1928年,距离新文化运动的辉煌岁月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倪焕之的形象正是“新青年”的模范:他追梦,奋斗,有时胜利,但后来,他感到困惑,试图妥协。最后他失败了,悲惨地死去。故事在希望与幻灭、理想和行动、渴望和绝望的循环之中循环不止。小说情节展示了一个封闭的回旋过程:主人公渴求实现他的理想,继而遭遇挫折、失败和致命的危机。这个情节模式将在现代中国“成长小说”中不断地出现。《倪焕之》描述了主人公一生的历程。
像这样一部专注于旅程之开端的意义的小说,与歌德(1749—1832)对威廉·麦斯特离家出走的描写、巴尔扎克(1799—1850)关于外省青年来到巴黎逐梦的故事和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为他笔下的年轻人物的个性成长所安排的远大前程极其相类。或者借用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的话来说,这类情节来自那一类描述青年成长的伟大小说谱系,这些青年总是“一开始就对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欲求,对它的复杂多变和它所做出的承诺感到强烈的困惑”。这个系谱即“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是小说叙事中特定的一类,聚焦于青年人的心理成长,包括自我修养、个性塑造以及在历史运动的背景之下去寻求实现理想的尝试。
作为中国的“成长小说”,《倪焕之》通过叙述一位同时试图改变自身生活和国家命运的新青年的生命历程,创造了一个将个体发展和社会革新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史诗。倪焕之还只是五四运动后现代中国小说中开始涌现的虚构青年人物中的一位;在他身后还矗立着现代中国作家塑造的一系列青年形象,包括梅行素(茅盾《虹》),高觉慧(巴金《家》),蒋纯祖(路翎[1923—1994]《财主底儿女们》)和林道静(杨沫[1914—1995]《青春之歌》),这只是一些最著名的例子。同时,在倪焕之年轻的身影背后,是少年中国辉煌、崇高的形象放射的光芒。现代中国小说民族主义话语中,青年这一核心象征符号,表达了对民族复兴的不息呼唤。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众多改良和革命运动始终不变的目标。
一般认为,成长小说的叙述规划,是将青年成长最后达成的定型塑造为代表特定理念的充分发展了的人格。但正如黑格尔(1770—1831)和卢卡奇(1885—1971)所说,这样的理想视景很少能够在现代小说缺乏诗意的散文化世界中得到明晰表达。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较为罕见的成功例子是,《青春之歌》(1958)能够演绎完整的目的论修辞;正如巴金早期无政府主义小说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历史境遇瓦解了小说原本意图强化作者政治信仰的叙事设置。例如,巴金的第一篇小说《灭亡》(1928)里,主人公为实现其理想而付出的努力,以自我毁灭而告终。在《爱情的三部曲》(1931—1933)中,巴金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对比表现得更为感伤而夸张,情节走向某种道德神秘主义,青年的成长被寓言性地诠释为“生命的开花”,但最终仍旧以青年的自我牺牲告终。
青年的牺牲或自我牺牲,通常被设定为中国成长小说的高潮部分。在现实生活中,李大钊于1927年光荣就义。他的殉难使他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一个道德楷模和不朽的传奇,最重要的是,成为中国青年人效仿的偶像。但李大钊并非现代中国青年史上唯一的烈士:二十年前,邹容(1885—1905),年仅20岁,就死于狱中,这位年轻的革命者被认为是革命精神的化身而名垂千古,他赢得了“青年之神”(孙中山[1866—1925]语)的不朽美名。邹容的殉难表明革命青年的牺牲如何为死亡赋予了高尚的意涵。然而,这些死亡被赋予的文化意义和关于年轻殉道者的文学再现,也同时暴露了旧时代革命青年自我成长当中永恒的冲突,那就是生与死的冲突——年轻生命的牺牲,得以使青春永恒,而在青春“永远”定格之际,也正是它因暴力而遭遇摧毁之时。
(本文在原书中题为《1916年9月1日李大钊诠释“青春”现代中国的“青年”之发明》。作者为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
作者:文/宋明炜 译/卢冶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李纯一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