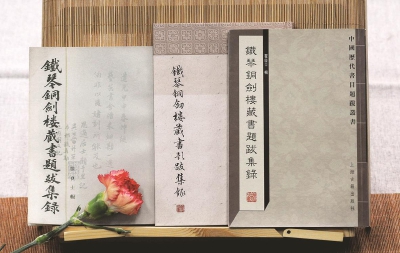
元刊本《通鉴》已知的最早收藏者是明代苏州大文豪文征明,之后在书边上留下痕迹的还有其长子文彭,文彭次子文元发,曾孙文震孟、文震亨。明朝亡后,《通鉴》因为亲戚关系转到严家,传入严虞惇父亲手中,之后历虞惇、鎏而传到严有禧。
江苏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由瞿绍基(1772—1836)于清中叶创始,乃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与齐名的皕宋楼等不同,瞿氏铁琴铜剑楼屡经丧乱(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而终未断绝,其大部分藏书于解放后由其第五代传人捐献给国家,现主要藏于北京图书馆,铁琴铜剑楼藏书传承之久、保存之善,在中国藏书史上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瞿启甲(字良士,1873—1940)是瞿氏藏书第四代传人,上世纪20年代,他在印行《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之余,令“儿曹”辈将古本中的历代题跋抄录出来,汇刻为《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一书。《集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是元刊本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的题跋,不仅篇幅最多(上海古籍1985年版中排印了27页),而且内容极其丰富。
初读此篇让人如堕五里雾中,因为它并不是一篇单独和完整的文章,而只是依卷次从书边逐条抄出的零篇碎语。尽管几乎每一条都记有日期和撰者名号(为此不得不对撰者表示赞赏),但仍然颇让人困惑:就日期而言,一则多用干支纪年,二则前后顺序紊乱,故而难以厘清;就撰者而言,一则非一人所作,二则一人多名,也难以识别。
不过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阅读体验,很像阅读我喜欢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作品。此翁惯于以不可知论哲学和强烈的符号学意识打造晦涩难解的文本,这种文本的特征恰如其分地表达在他的一部小说的标题中——《在迷宫里》。罗布-格里耶的小说也是由含义不确定的片段构成,而每个不完整的片段又用复杂多元且同样不确定的关系扭结在一起,于是阅读就成了如同侦探破案一般。
当然,类比只是类比,《元刊〈通鉴〉题跋》并非人为臆造,其独特的非线性结构是线性时间和线性文本在久远的相互作用中自然形成的,而随着阅读者“以意逆志”的“解构”和条分缕析的“重构”,它的本来面目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处于谜团核心的“主要人物”叫严虞惇(1650—1713),常熟人,清初名士,题跋中或署名为“思庵”、“草草亭主人”。《清稗类钞》“散体文家之分派”一条记:“国初……士大夫以文名者,则推李光地、潘耒、孙枝蔚、朱彝尊、严虞惇、姜宸英诸人。中惟虞惇文陶铸群言,体近庐陵、南丰……余多不入格。”按庐陵为欧阳修,南丰为曾巩,论者将虞惇与之相比拟,可见其格调之高。
严虞惇13岁就开始读《通鉴》,而读这个版本的最早记录是1676年,最后记录是1710年,也就是说:从26岁读到60岁,这本书的阅读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儿子严鎏感叹道:“昔司马文正公云:‘某修《通鉴》,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而先君子披阅至六七不厌,其精勤为何如,即此书而于他书可知也,我子孙其永念之哉!”
按《清史稿·文苑传》有一篇《严虞惇传》,仅寥寥百来字,极其干瘪、乏味;而《题跋》中却留下虞惇一生中许多吉光片羽的生活点滴,其生动真挚处,足以让一个早已湮没在历史记忆中的古人在读者眼前复活。
虞惇早年随父宦游,康熙三十六年(1697)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中间一度因科场案牵连罢免,后复起用,历官国子监丞、大理寺副卿等职,累迁太仆寺少卿。
虞惇虽然从26岁起即反复披阅《通鉴》,但真正的通读却要到1701年才第一次完成,当时因科场案,“摘官,索居无事,遂得终卷”,并辑出《通鉴提要》一书。此书在1710年最后一次读《通鉴》时又重新校订过,不过今日似乎已经失传。
1701年前后是虞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穷居京师,“索逋如猬,突烟不举,人生苦况,至斯而极,未来茫茫,作何归宿,可为太息也”。然而,令虞惇颇为自负的是,自己在如此境况下还能读书:“于如此窘迫中,尚能执笔披阅此书,谚云‘黄柏树下弹琴’,亦可想见余之胸次矣。”
1702年,虞惇不幸患病:“卧至三鼓,心痛大作,吐血数口,恐是死症,如何!”此后约过一年才重拾书册,病已早愈,而另有一桩大变故:“阅前记为之怆然。去年以十四日夜心痛呕血……几不能生。赖武陵君昼夜扶持,废寝食,奉汤药,逾月而复故,今武陵君先我而逝矣。昨赴东川师席回,空房无人,失声长恸,今复见前记,心摧胆裂,哀如之何。”这样沉痛感人的闺闱之情在“正史”中绝对是缺席的,只有在这种不成文章的私人文字中才能找到。
虞惇被重新起用后,曾任大理寺副卿达5年以上,于是在1708年至1710年间的题跋中留下很多案件的记录。1710年大灾,在“通仓偷米”案审理中,“提督必欲诬入无辜五人于死”,而“邢部满汉堂遂互相推诿,殊失大臣之体”,虞惇在题记中讽刺道:“《诗》云:‘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言小人争知而让过也,有旨哉,有旨哉。”
因为不肯附会当权者冤杀无辜,虞惇面临“降级调用”的危险,他在《通鉴》卷一百五十二后记下这样的感想:“呜呼!以不肯杀人媚人而降调,不贤于一岁九迁乎?盖自是而余浩然之归志决矣。”呜呼,虞惇的志节和不惜以人血染红顶子的酷吏相比,真可谓宵壤云泥哉!由此可见,读书纵无补于世道,毕竟还是有补于人心的。
总体灰暗的基调中,也有一些有趣的片断。如1710年中秋的一条:“传闻七月初六日淮扬之间雷霆风雹大作,有十二龙盘旋空中,如战斗状,鳞爪历历可见……亦异事也。”古代的神怪记今人往往当成神话看待,而在当时人们眼中,却是有根有据的实录,此例可为一证。同年七月的一条:“初患右耳聋,甚闷闷,知五官不可缺一也。”耳聋并不有趣,而最后的按语却颇可爱,有黑色幽默效果。
虞惇在书边留下的零星感触,如今看似平常,而在文网密织的清代,却是潜在的祸患,经历过科场案的他对此十分清楚:“中间评语,多有棖触,伤忌时事,但可藏之家塾,不可传示,凡我子孙记之。”
在虞惇之后,他的儿子严鎏又于1733年、1737年两次通读该书,并留下大量题记。如果说虞惇的题记多半只是借书边写的日记,那么严鎏在1737年腊月记下的这段话则是书本与阅读书本的人的生活相互渗透的一个例子:“自古治日少而乱日多,然未有如唐僖宗时者,藩镇无一人不叛,天下无一块净土。阅史至此,怨愤欲绝矣,加以岁暮诸逋猬集,天又阴雨,昼夜不止,岁月几何,堪此三闷于一日!”
如同科幻电影中不同时空中的人借助某种道具(如照片)而相遇一般,父子两人在书页边上找到跨越时间阻隔而相接触的通道。在《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后,虞惇于1700年记下:“时方绝粮,今日从逆旅主人借米五升,度过一日矣;明日以后,不知作何活计也”;33年后,严鎏在拜读“先人手泽”后感慨道:“读先大夫庚辰所记,时适罢官,淹滞京师,穷况至于此极。今日所遭,正复不减,可谓叹息流涕也。”
又,卷二百四十四后,虞惇记:“余于此书披阅已数过矣。今年马齿亦六十有一,未知此后更能再一阅否?”而严鎏所记为:“睹先君前记,不禁泫然,盖自庚寅后,于此书亦不能再阅矣。
对于当时的虞惇还是不确定的未来的疑问,对几十年后的严鎏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历史,而两者竟吊诡地并置在一处,这不免让读者生起无尽的深思。
而就在同一页上,竟还有一个更为奇幻的时空“错乱”。那是另一位更早的读者、明代的文元发(文征明的孙子)与自己的四次相遇:“甲申年(1584)九月初七日申时四休斋记。庚寅年(1590)八月初四日申刻再记。视前记恍已七年。日月如流,老景渐增,不知此后眼目如何,尚能一再阅否?丁酉(1597)十一月十一日再阅,时年六十九。发。庚寅岁笔记谓:‘不知此后尚能一再阅否?’不意越八年而丁酉再阅一遍,又四年而辛丑(1601)又复一过,真日月如流,固不知老将至而耄及之矣。漫记此以验此后目力,尚能涉猎否也。正月十有八日,时年七十有三。”
博尔赫斯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写老年的自己和青年的自己跨越时空相遇并交谈,其构思之奇诡令读者惊艳。而结结实实地把《通鉴》读了四遍的文元发一生中竟三次在时间之流中与自己相遇,这不得不让人感叹现实永远比虚构更奇幻。
不过,1601年的文元发当然不可能像无所不知的小说叙事者一样,知道这次阅读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更不可能知道仅仅一年后,他的儿子文震孟就读到了这段题记并为之“悲恸”——此时,他自己已经辞世,而儿子文震孟也已不幸地成了“孤孟”。
元刊本《通鉴》已知的最早收藏者是明代苏州大文豪文征明,之后在书边上留下痕迹的还有其长子文彭,文彭次子文元发,曾孙文震孟、文震亨。明朝亡后,文震亨绝食而死。《通鉴》因为亲戚关系转到严家,传入严虞惇父亲手中,之后历虞惇、鎏而传到严有禧。在全书最后一卷后,严有禧留下一段总结性的话:“惟是书向藏文氏,后传吾家,名贤之遗迹存焉,先人之手泽在焉,亦一家宝玉大弓也,凡吾子孙其共守之,其共珍之。乾隆壬申(1752)六月十三日。有禧谨识。”
和铁琴铜剑楼的大部分善本藏书一样,这部书如今就藏在国家图书馆。这一点既不足为奇,又令人震惊:这样一个记录了湮灭在明清两代几百年历史中的一些普通读书人的极度私密的阅读和生命体验的载体,这样一个能让不同时代的人们穿越时空相聚一堂的场所,这样一个极具后现代互渗、自涉特征的奇特的前现代文本,果真以雕版印刷的宣纸的形式、实实在在地存在于21世纪的现实世界中的某个角落里吗?如果这个角落真的存在,我想它的名字只能是——“永恒”。
作者:沙门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