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游记
(之一)
《文汇学人》2017.07.14
文/谷崎润一郎 译/徐静波
“我最想要知道的,便是从宫崎君那里听来的有关日本的作品被大量译过来的情形,我想了解其范围的种类。我表示说,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他们尽量帮我把这些译本收集起来,我带回去作为赠给日本文坛的礼物。”

谷崎润一郎
内山书店
过了数日,M君带我去了位于北四川路上阿瑞里内的内山书店。据说这家书店是除了满洲之外中国最大的一家日本书肆。店主是一个精力旺盛、明白事理、说话风趣的人。在店堂里侧的暖炉边,放置着长椅和桌子,来买书的客人可在此小憩一会儿,喝杯茶聊会儿天,——盖此家书店似已成了爱书者的一个会聚地。——我在此处一边喝茶一边听店主讲述中国青年人的现状。听店主说,这家店一年约有八万元的营业额。而这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由中国人买去的。而且这一比率每年都在增加。问道中国人主要是买哪一类书,说是没有定准,什么书都有人买。哲学、科学、法律、文学、宗教、美术……如今中国人的新知识,差不多大部分都取之日文书。当然不限于日本的内容,西洋的知识也通过日文译本在阅读。这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上海乃一个商业城市,虽也有卖西洋书的书店,但书的种类有限,他们所期望的原文书不易得。有时想要获得西文原著,就向东京的丸善书店去询问订购。还有个原因,便是语言的问题。日语要说虽不易,但只是阅读的话,与英、法、德语比较起来,其难易程度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要体会小说和戏剧的内蕴,也只须花上一二年时间,而只要是粗粗读懂科学和法律方面的书,有半年左右也就差不多了。因此,为了快捷地获得新知识的中国人,都在争相学习日文。译成中文的西洋书籍,很多是从日文本重译的。而所谓的新小说,仔细看一下的话,里边似乎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日本小说中获得启示,或者据日文小说编译的。——也就是说日文在现在中国的作用,正如同英语在当年的日本一样。“所以现在能读日文的中国人有多少弄不清楚。我的店里每天也有中国人来买书。然后在这儿喝杯茶聊会儿天回去。”
——内山书店就是一家向这样的中国青年人独家提供新知识的书店。就这样,在其他方面姑且不论,至少在文学方面,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在社会上最受认可,一个个渐次成名,称霸文坛。由此缘故,中国文坛对于日本文坛所熟知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在商务印书馆内,帝国大学毕业的文学士有六七个人,他们在不断地注视着东京的出版物。听说他们准备计划有组织地翻译出版日本现在的小说戏剧。

1930年代的上海北四川路
“你们那边对这些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吧。”内山氏说。
“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国后是如何开展活动的呢?后来成了政治家和军人的人多少还了解一些,而对那些从事文学艺术的人的情形,国内的人一点都不知道。这实在是很遗憾的。我们以后再进一步互相联系好么?今天也有中国的文人来过,说是听说谷崎先生到上海来了,务请介绍一下。您光临上海一事,前两天中国的报纸都报道了,有很多人想见见您。于是我就说,行,过几天我去请谷崎先生,举行一个见面会,把主要的人聚集起来认识一下。我想近日就举行这样的活动,届时务请光临。”
在中国竟然有这么多的知己,这实在是没有想到,我恍如做梦一般。那时我才知道中国的报纸上已有了我的报道(此后我也曾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西条八十氏在归国的途中路经上海的消息)。
然后内山氏举出了新文学家的三位代表人物谢六逸、田汉、郭沫若。谢君研究日本的古典文学,目前正在翻译万叶集和源氏物语。有时来到这家书店,询问万叶集和源氏物语中的一些难解之处。“等一下,这些东西我也搞不懂。”据说内山氏也常常不知所措。田汉君翻译过《日本现代剧选》(这似乎是要分作第一集、第二集这样连续出版下去,现在仅出了第一集,即菊池宽剧选)。此集由《父归》《屋顶上的狂人》《海之勇者》《温泉场小景》四篇组成,卷首有“新思潮”同人的介绍,译者记述了以前曾听过冈本、小山内、里见、菊池、久米[此处,当指冈本绮堂(1872—1939),日本剧作家、小说家,刊有《冈本绮堂戏剧集》十四卷;小山内薰(1881—1928),戏剧艺术家、剧作家,日本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刊有《小山内薰全集》八卷;里见淳(1888—1983),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善心恶心》《多情佛心》,刊有《里见淳全集》十卷;久米正雄(1891—1952),日本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剧本《牧场兄弟》等]诸人演讲的回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了。此外他在戏剧创作方面,已出版了一本收有五个独幕剧的戏剧集,题为《咖啡店之一夜》(《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获虎之夜》《落花时节》)。其中的《获虎之夜》被认为是一篇杰作,听说近日同文书院的学生准备在日本人俱乐部的舞台上试演这部作品。郭君虽是福冈大学[译注:应该是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出身的医学士,但并未在医学方面深入用功,而是一味地将精力花在文学上,被称为“中国的森鸥外”。——这样一说也许有人会认为他已是位有相当年岁的老人了,自然并非如此。与木下圶太郎氏[木下圶太郎(1885—1945),日本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诗集《食后的歌》等,刊有《木下圶太郎全集》二十五卷。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确如谷崎所述,比木下小约十岁左右]相比还要年轻十岁以上,与田君谢君一样,都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所以他们的出名还就是最近的事,在出名前曾经历了相当的艰辛。尤其是郭君,在福冈时代娶了一位日本女子作妻子,且已有孩子,有一个时期甚至苦于无钱买柴米,是从穷困中苦斗过来的。内山氏说:“郭君好像夫妇间非常恩爱,膝下有这么多的孩子要养育,竟一直坚持到今天,郭君自然很了不得,那位日本太太也实在很令人感动。”后来我听同文书院的教授讲,在所写的文章中受日文影响最多的是郭君。听说他既作诗又写小说,在外语上通晓英语法语德语,从这些方面来说,也真可称为“中国的森鸥外”。

森鸥外(1862—1922),日本近现代最大的文学家之一,以其创作、译作和评论为日本新文学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贡献。亦是医学出身。刊有《鸥外全集》三十八卷。
上述的三人当然都要出席见面会的。其实中国的文坛上也分成各种各样的派,谢君的一派与郭君的一派彼此似乎多少也有些歧异,恐怕会出现微妙奇异的场面,但是来应该是没问题吧。此外与他们在领域上稍有些不同的欧阳予倩也来,他是新剧运动的旗手。此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既当演员也当导演,最近还在从事新电影的制作。似乎是集小山内薰氏和上山草人氏[上山草人(1884—1954),日本现代表演艺术家,曾担任《浮士德》等的主演,有自传小说《蛇酒》《炼狱》]于一身的人物。会场设在内山书店的二楼,由于无法容纳所有希望见面的人,内山氏说打算先在当天邀请重要的十来人。
内山氏的这一主意,对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我深深地感谢他的这片好意,并请他多多费心。
{日本在1886年制定帝国大学令,依此,1877年创立的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1897年,设立京都帝国大学时,东京的帝国大学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谷崎润一郎第二次访华时的1926年,已另建有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和北海道帝国大学,但本文中的帝国大学,大概主要是指东京帝国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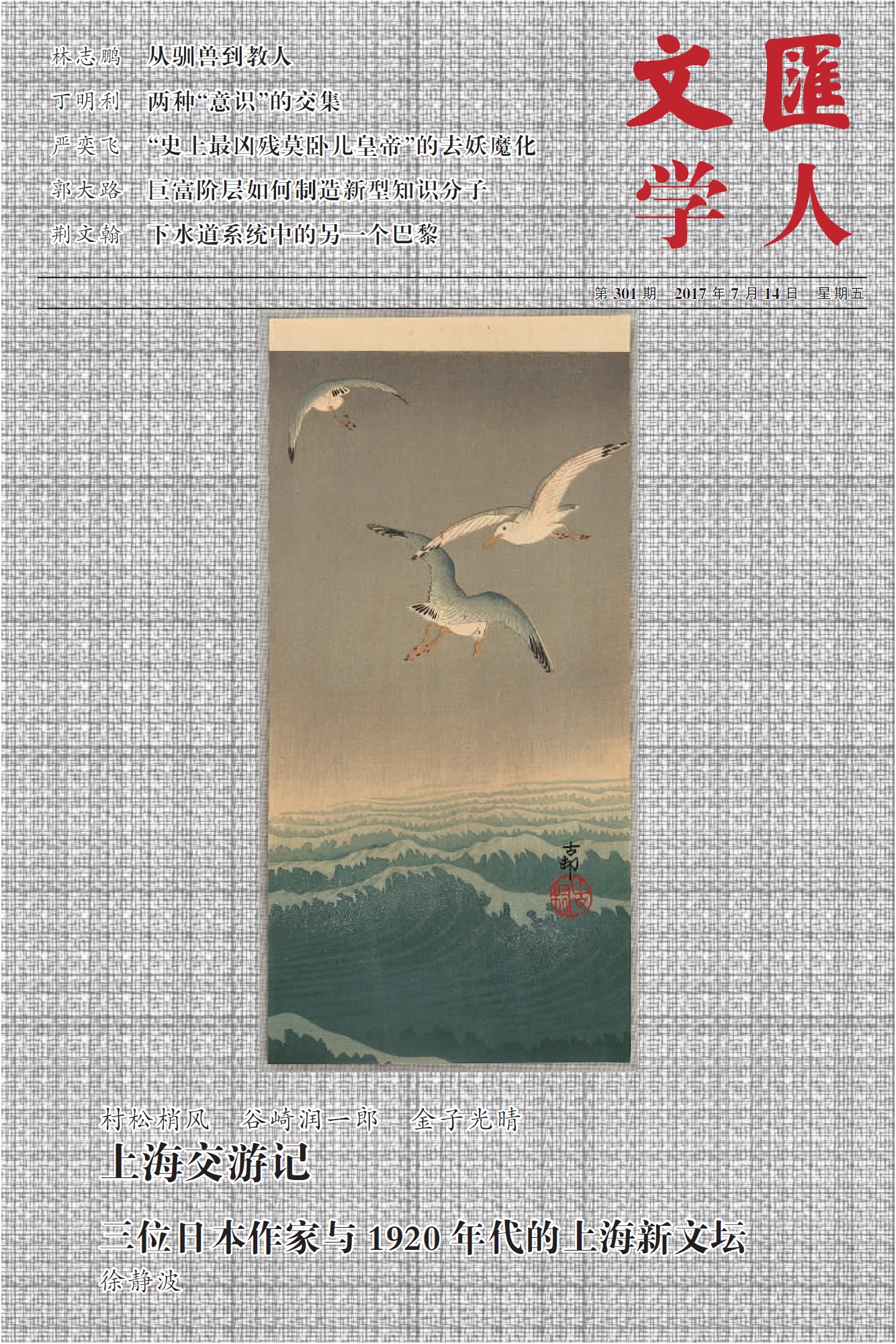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李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