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 | 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
(七)
七、性与宗教精神
除了鸠摩罗什的天才,破色戒是中古鸠摩罗什传记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他的传记资料所记载的有关他与女性之间发生性关系的共有三次事件。僧祐和慧皎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提到了其中的两个:第一件事发生在后凉将领吕光于384年征服并占领龟兹之后。据说,这位将领觉得,作为一位享有智慧美名的重要人物,鸠摩罗什实在太过年轻(关于这一点,在我们讨论有关鸠摩罗什卒年的争议问题时还将提到),他决定以通过强迫他与龟兹王的女儿发生交合来考验他。[69] 一开始,鸠摩罗什进行了强烈的反抗。但在他被强灌下了大量的酒,并和那位公主一起被锁在一间房中之后,他终于屈服;第二件事发生在多年以后,当时鸠摩罗什已在长安被后秦姚兴奉为国师。姚兴对鸠摩罗什说,大师既然被赋予了如此非凡的智慧,如果不能传递自己的“法种”,真是太可惜了,“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从这以后鸠摩罗什就“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丰盈。” [70] 《晋书鸠摩罗什传》中也提到罗什在后秦破戒,其中包含了鸠摩罗什破色戒的几次经历中听来最为不堪的一次:
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有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鄣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71]
在这一事件中,鸠摩罗什显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不顾戒律的约束。无论从佛教还是中古世俗伦理的角度,这种在如此庄重的场面上公然提性要求的做法,都可以说是骇人听闻的,在有关南北朝佛教高僧的记载里大概只有关于昙无谶的性丑闻可以与之相比。[72]和僧祐慧皎所提到的两次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两件事中,鸠摩罗什是被逼破戒,尚可以说是世俗权利的牺牲品,但在这件事中,他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在《晋书》的文字里,姚兴向罗什提供宫女发生在罗什奇迹般的“一交而生二子焉”之后,所以似乎姚兴的行为也有顺其所好的成分在内。我们无从知道《晋书》的编纂者是通过什么材料获知这一事件的。[73]但是我们很难说,在唐代官方史家所撰的鸠摩罗什传中出现这样的内容是出于排斥佛教的目的。《晋书》的编纂者对鸠摩罗什的描写除了提到破戒的一处,其他的方面都很明显是赞扬的,这一点上和佛家的立场并无很大的不同,而且《晋书》的整个传记明显是将僧祐慧皎的传记缩略而成的,而非另起炉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晋书》编者还特别通过鸠摩对罗什具有的超自然力量的强调来为其所作所为辩护。《晋书》接下来说,通过一场吞针的比赛,鸠摩罗什向那些效法他而为自己建立起家庭的僧侣提出挑战。他拿来一大把针当众宣告说:“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 接着,就像吃正常的食物一样,咽下了大量的针。其他的破戒者惭愧之余,马上结束了他们那种罪孽的生活方式。所以《晋书》的编纂者们实际上很明显是要向读者说明:罗什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僧人,因此,传统的规定和制度并不适用于他。虽然大乘教义中的“方便”(upāya)观念无疑影响到了《晋书》编撰者对鸠摩罗什的描绘,但我推测《晋书》作者之所以要特意加入罗什这种放肆的性要求及与之有关的吞针比赛,主要还是为了符合古代官修史书中为僧道立传的某种标准。僧道的代表,无论他们在各自的宗教上贡献如何,到了官方史书里,大都只能归入〈艺术传〉或〈方技传〉等范畴,与医筮卜祝之类的人物被归成一类。所以编撰者就往往需要突显传中人物的“变化伎术”的能力。[74]对罗什的这种描写正是当时读《晋书》的人所能够预期的,和对罗什的褒贬关联倒反而不大。
然而,对于中古中国的佛徒来说,鸠摩罗什破色戒的经历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以鸠摩罗什这样的地位而不守戒律,的确会对僧侣生活中最重要的独身原则造成损害,而且也会让人对质疑罗什所提倡的教义思想的效力。针对这种质疑,七世纪时的名僧道宣就在他的《道宣律师相感通传》中对这一争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余问:“什法师一代所翻之经,至今若斯,受持转盛,何耶?” 答云: “其人聪,善解大乘。以下诸人皆俊,又一代之宝也。绝后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译以悟达为先,得佛遗寄之意也。” 又问: “俗中常论,以沦陷戒检为言。” 答:“此不须相评,非悠悠者所议论。罗什师今位阶三贤,所在通化。然其译经,刪补繁缺,随机会而作。故大论一部,十分略九。自余经论,例此可知。自出经后,至诚读诵,无有替废。冥祥感降,历代弥新。以此诠量,深会圣旨。又文殊指授令其刪定,特异恒伦。岂以別室见讥,顿亡玄致,殊不足涉言耳。” [75]
上面的这段问答中,道宣虽然谈到鸠摩罗什犯戒的问题,但议论的重点其实都是要对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典作出评估。文字中包括的两个问题主要围绕相关的两点。第一,罗什的翻译,在当时一些佛徒眼中并不很完整和精确,却为何能越来越被普遍接受?第二个问题问得很简略,但是该问题的言外之意可以从道宣回答的特殊针对性看的很清楚。众所周知,鸠摩罗什在翻译佛典时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经文进行删改,也就是道宣答复中说的“故大论(指《大智度论》)一部,十分略九。自余经论,例此可知。”。当时社会上不少对他这种处理经文的方式感到不满的人,似乎都将他“沦陷戒检”的行为与他不忠于原典的翻译态度联系了起来,而据此提出非难。道宣毫不迟疑的回答说鸠摩罗什“沦陷戒检”决不影响他所译佛经的正确和权威性。他的根据出于两个方面,首先,鸠摩罗什智慧过人自然不用说,连他的弟子亦复如是,所以翻译“以悟达为先,得佛遗寄之意”;其次,从罗什的时代以来,对他译的佛经的诵读已使“冥祥感降”,而他对经文做出的刪定也是出自文殊的指授,所以这些译本不能用一般佛教的规则来衡量。既然这些译本的效力也已经被大量奇迹应验,那么就不应对之有所怀疑。罗什“以别室见讥”是“悠悠者”的议论所致。对戒律提倡最不遗余力的道宣之所以会对罗什破戒做出这样全力的辩解,与其说是为了维护罗什的地位,不如说是为了维护罗什所译的佛经的权威地位,因为这些经文的有效与否对道宣来说至关重大。他大力宣传的诵经能引起感通就和这些译本有直接的关联。
到了九世纪初,一位很博学的僧人神清在他的《北山录》也中对鸠摩罗什的破戒行为进行了评述。该著作中〈合霸王〉一篇讨论的主题是世俗权力与佛教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在提到罗什受吕光和姚兴之逼的例子后,神清评论说:
净行者耻闻其事。夫宋龟灵而纳介,荊人辨而召刖,岂非智有所可,力有所困乎?故继益以损物,莫为之不惑也。魏孝文诏求什后,既得而禄之。虽吾教以仆陷大谲,然春秋之义,言功十世亦可宥也。初童寿在外国遇圣者,告之曰:‘若慎无适东土,将有大不利焉。’ 什乃不顾而来, 启非良臣死国计? 良执死高义。仁者死成仁。何顾之有也。故什死,焚之心舌不烂焉。[76]
照神清的意见,罗什虽然“仆陷大谲,”以至于使“净行者耻闻其事,”但却是可以原谅的。他的这种悲剧其实就是“有限的智慧”(limited wisdom)所产生的结果。就如古代能识别宝玉的卞和与能预卜未来的神龟都不能逆料他们的能力会给自身带来何种灾殃一样,罗什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学识和智慧将给他带来何种危险。强调儒佛道融合的神清更进一步表示,如果用《春秋》大义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以鸠摩罗什传播佛教之大功,其破戒是可以原谅的。更何况鸠摩罗什为了来中土传播佛教,没有理会事前得到的警告,所以是“良执死高义。仁者死成仁”的行为。[77] 神清用指责吕光和姚兴这样的世间帝王的胁迫来为罗什开脱,在这一点上他的议论固然没有太多新意,但是他能指出鸠摩罗什的智慧和他的遭遇之间的诡吊性关联,眼光却非常独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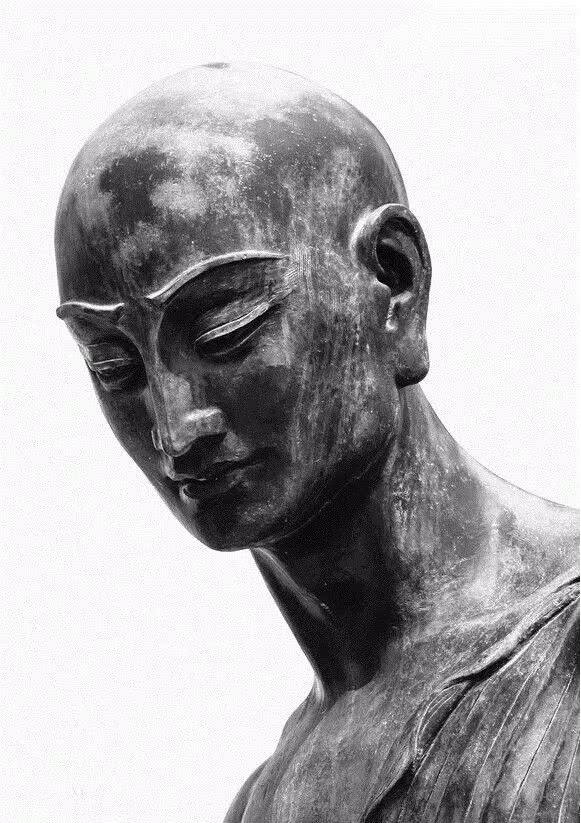
和古代的佛教僧人不同,现代的研究者对罗什破戒一事的兴趣似乎主要是希望从中了解当时社会的佛教实践的一些面相。例如柯嘉豪(John Kieschnick)注意到鸠摩罗什与龟兹公主的结合过程,和他父母鸠摩炎和耆婆之间父母的结合一样,都是被胁迫的结果。所以他推测说破色戒的那些经历也许是“三则被歪曲了的传闻的凑合”(an amalgamation of three distorted legends),而这些传说的流行可能说明中古社会佛教徒对禁欲的普遍漠视。[78] 也就是说,佛教僧人中破色戒的恐怕不少。当然这是从叙述的内容上去推断它们反映出来的外在现实成分,并强调佛教的理想和实践中存在的巨大差异。这样做固然有价值,但是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这些情节在整个叙述结构中起倒了什么样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它们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时空场合出现,而作者又是如何利用它们来表现鸠摩罗什的个性。[79]
尽管僧祐与慧皎没有怎么就未能控制自己性欲一事指责罗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忽视了这些破戒行为对其形象与遗产所产生的影响。和《晋书》不同,僧祐和慧皎都没有试图利用“方便”或“不二”这些现成的佛教理论来捍卫鸠摩罗什的尊严,而这些理论恰恰又都属于罗什所提倡的大乘教义中最基本的观点。所以如果他们要那样来辩护的话是容易做到的,而且也能为当时大众所接受。不管在龟兹发生的破戒事件是否具有任何历史真实性,我都想指出的是:僧祐和慧皎之所以将其记录在他们所撰的鸠摩罗什传中,是为了让读者注意到罗什生命中存在的这个污点,以及形成这个污点的深层原因。他们表现出的这种不愿为尊者讳的批评态度在五世纪的佛教作者之中似乎相当有代表性。比如写《名僧传》的宝唱,他给罗什写的传记虽然没有留下,但从宗性摘抄的内容中,我们发现宝唱似乎也想通过探究鸠摩罗什之心理,对其性欲作出解释。请看如下几句话:
梦释迦如来,以手摩罗什顶,曰:‘汝起欲想,即生悔心。’
由于没有上下文,我们无从得知宝唱在整体上是怎样处理鸠摩罗什的破戒行为的。但上面这寥寥数语却提供了一些线索。用罗什的梦来谈他对性欲的克制是很有创意的,而且作者似乎是想说明,这种性欲的产生责任在罗什本人,所以他才会得到释迦如来佛的警告。[80]
现在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一则关于鸠摩罗什生涯的预言的话,那么僧祐慧皎对破戒问题的诠释就会变得清晰。传记前面的部分曾经提到,鸠摩罗什十二岁时与他的母亲回龟兹,路途中在月氏北山遇见了一位罗汉。罗汉告诉耆婆,她的儿子需要受到极为小心的保护:
若至三十五而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掘多无异。若戒不全,无能为也,正可才明俊义法师而已。[81]
这个预言自然是传记作者们编织的结果,但却很有深意。他们试图在鸠摩罗什破色戒的行为与其“平凡”的生涯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并借此给他的一生作宗教上的定位。[82]在慧皎他们看来,如果鸠摩罗什没有犯下这个罪过的话,他绝对应该会成为另一位以“坐禅第一,大化众生”闻名的优波崛多(Upagupta),[83]也就是能够真正以自身表率来弘扬佛法,达到佛教实践的最高理想,而不只是一个“才明俊义法师”。所以鸠摩罗什所完成的诸如译经等等工作,在一般人眼中固然很了不起,但其实还不是最高的境界。我们虽然无法确定鸠摩罗什生卒之确切年月,[84]但这和我们这里的研究没有关系,因为从他们的叙事结构来看,僧祐也好,慧皎也好,他们都相信鸠摩罗什是在三十五岁之前破戒的。[85]因此,就像预言所说的,等待他的将是令人惋惜的那一种命运。他们将这一预言放在鸠摩罗什完成了佛教经院完整的教育之后和获得更高的学问(即大乘教义)之前,似乎表明未来的道路是由他自己来选择的。同样,他们将鸠摩罗什的失败与优波崛多之成就并提,也表明罗什的最终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努力而非佛家因果支配的结果。如果他能有真正的“不退转”的定力,那么结局就会不同。插入这一预言也是为了回应鸠摩罗什的天才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以及他的不受拘束的个性和僧侣规则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鸠摩罗什那闻名于世的非凡智慧对他而言,既是一种恩赐,也是一个诅咒。就像神清所暗示的,正是由于罗什那种神童般的天才,才会让吕光起了疑惑,想要考验并打破了罗什的持戒。同样姚兴之所以强迫他娶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这位大师之非凡智慧的赞赏。所以在这里智慧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和鸠摩罗什所掌握的佛法的内容不能混为一谈。
通过对故事的巧妙组合,僧祐和慧皎进一步强化了罗什才华之杰出和他破色戒之行为的严重性之间的对照。他们的这种看法也表现在他们所撰写的〈佛陀耶舍传〉中。当听说鸠摩罗什在姚兴的催逼下娶妾的事后,佛陀耶舍发出的感叹最为一针见血,也最能表达佛教史家对罗什的个性的看法:“罗什如好绵,何可使入棘林中?”[86] 这话再次凸显了鸠摩罗什缺乏沉毅坚定的个性,也可以印证本文前面对耆婆对罗什的作用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慧皎沿用了僧祐的看法,同时也进一步指出:是因为来中国传播佛法,罗什才会犯下破戒的罪过。这一点可以从慧皎特意加入的鸠摩罗什和他母亲的临别对话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段对话上文已经提过,这里就不再摘引。尽管僧祐和慧皎对罗什破戒不无同情,但他们两人都坚持让鸠摩罗什从他自己的口中不断表达出很深的悔意。比如他要求他人把他看作是出淤泥的莲花,也就是要只取其可取,而非全面模仿。他和卑摩罗叉的对话就更加说明问题:
初什在龟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入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问什曰:“汝于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 什答云:“漢境经律未备,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敬耳。”[87]
罗什的答复就像是忏悔词,而且是向传授自己戒律的老师作的。其中“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敬耳” 一段自白,更是僧祐和慧皎借了罗什之口来剥夺了他能成为佛教理想中的“师”的资格。[88]这是非常严厉的裁决。这里的“师”应该是戒定慧三者缺一不可,能像优波掘多那样“度无数人”的宗师,而不仅是“法师”而已。因为在僧祐和慧皎看来,义学方面的精深固然能让罗什传“法”,却并不能抵消他的“累业障深”。佛雷(Bernard Faure)在研究佛教与性的问题时曾总结说:在佛教的辩辞中,对“性”的处理大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的“道德上的模棱两可说”(morality of ambivalence ),比如在大乘教义上有所谓的真俗二谛,在戒律上有在家出家两套,而“方便”之法门得到广泛运用等等;另一种是“由故意破戒而获得解脱说” (transcendence through transgression),比如密宗修行之类。[89]但是佛雷说的这两种情况在这里都用不太上。相反,僧祐和慧皎以“性”为切入点来揭示人性存在的困境,并显示出学问与实践有时并不相一致。这种“法”和“律”的关系颇有点像后来儒家传统中“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僧祐和慧皎在他们的叙述中或许还暗示说鸠摩罗什的破戒行为也影响了他说服不信佛教者(即吕光和他的朝廷)的力量。在第一次破戒后,罗什在凉州吕光的宫中被囚禁了十六年,在此期间,他似乎在宣扬自己的信仰方面少有建树。照理说,罗什的传早已提到他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但通篇唯一一处提供了能够证明这种本领的具体事例的地方就只有这个关于他在凉州的部分,有趣的是这也恰是他一生经历中最失败的一段。现代学者常常凭着这段的描写就推论说鸠摩罗什在凉州时的身份不是佛教的国师,而是政治上的顾问。[90]这样的推论是很有问题的。当然这段描写也许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现实,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在传记的这个部分,僧祐和慧皎选择将焦点完全放在鸠摩罗什的预言本领上。在佛教徒传记中,超凡的预言能力往往就是宗教力量的同义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佛图澄利用了这种能力来使后赵野蛮的统治者转信佛教。鸠摩罗什却没有取得任何类似的成就。事实上,同是预言家,慧皎笔下的鸠摩罗什与佛图澄之间的差异却是不能再大了。从传记来看,罗什所作出的预言即使结果不断清楚地证明他的正确,后凉的统治者依然没有因为这种能力而为他所感化,成为佛教的信仰者,换句话说鸠摩罗什没能充分利用这种能力来使人皈依佛法。那么僧祐与慧皎在这里是否想给他们的读者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鸠摩罗什的破戒使他在不信佛教的俗人面前丧失了道德上的权威呢?我想我的推测就只能先到这里。
-----------------------------
[69]原文是:“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 (《大正藏》:2059.331c04)。龟兹被洗劫后,白(帛)震成为了新的国王。传记没有明确指出这里所说的国王是被吕光废黜的白(帛)纯,还是他新即位的弟弟白(帛)震。上引文中的“未測其智量”一语从字句上看似乎是指吕光不了解罗什的智慧究竟到何种程度,但根据僧传,吕光早在出征龟兹之前就从苻坚那里了解到了罗什的非凡才智,所以当此刻看到的是如此年轻的一位僧人,才产生怀疑。
[70]有关鸠摩罗什留有后裔的传闻在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497年,北魏孝文帝下诏表示要寻访照顾鸠摩罗什后嗣的意愿。诏书说:“ 罗什法師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尤有遺地,钦悦修踪,情深遐远,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又见逼昏虐,為道殄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叙接”,参看《魏书》卷一一四,第3040 页。北魏政权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大概出于两种目的,一是为了表示自己是鸠摩罗什留下的佛教遗产的真正继承者,二是贬低被其推翻的北方其他胡族政权。
[71]《晋书》卷九十五,第2501-2502页。
[72] 有关昙无谶这方面的记载,见《魏书》〈卢水胡渠蒙逊传〉:
始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涼州.蒙遜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妇人,蒙遜诸女、子妇皆往受法.(《魏书》卷三十六,第2208页)
[73]诺贝尔认为这个情节是《晋书》编纂者插补的,因为这与姚兴后来强迫鸠摩罗什娶十个宫女的做法相矛盾。参看诺贝尔, 〈鸠摩罗什〉,第226页, 注第2。伯希和不同意诺贝尔的观点,认为他对“少嗣”一词的理解有误。伯希和说这个词不像诺贝尔理解的那样,表示“没有子嗣”,而是“子嗣不多”的意思,这样就照应了他在宣讲佛经过程中与宫女结合而生二子的情节。所以姚兴会想让这位大师有更多的孩子。而且,伯希和似乎认为这个情节本来就载于某部传记,而《晋书》的编撰者正是从这部传记中提取材料的。参看伯希和,〈鸠摩罗什研究札记〉,第6-7页。伯希和对“少嗣”一词的解释虽在文句上可以说通,但也很牵强,因为僧祐和慧皎都只提到姚兴认为不可使“法种少嗣”的情节,而从他们的叙述的语气来看,“少嗣”都是指的没有后嗣的意思。同样伯氏认为《晋书》中的那篇传记是根据《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之外的一本传记写成的观点也不具说服力,因为《晋书》与后两者中的鸠摩罗什传存在者惊人的相似。
[74]《艺术传》也作《方技传》。例如,玄奘、神秀和一行等著名唐代僧人的传记也都是被收在《旧唐书》的〈方技传〉中。
[75]《大正藏》:2107:437c22-438a05。唐朝僧人僧祥也在他的《法华传记》中也引用了道宣的评论,参看《大正藏》:2068.52a13-21。日本僧人教界也为鸠摩罗什作了辩护,只是他误将鸠摩罗什的弟子当作了他的子嗣,这也许是一个无心之过,因为日本僧侣经常带妻修行,并生育后代,让他们继承自己的衣钵。佛瑞(Bernard Faure)认为日本僧人根本就不认为鸠摩罗什破色戒的行为有何不妥,参看佛瑞:《红线——佛教对性的处理》(The Red Thread: Buddhist Approach to Sexu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第191-192页。
[76]这一评述收在《合霸王》一章中。《大正藏》:2113:589c03-22。
[77]卞和献玉的典故出自《韩非子》;神龟的典故则出自《庄子》〈外物〉。
[78]柯嘉豪:《高僧》,第18-19页。佛雷在他关于佛教对性之态度的广泛讨论中也持相似的观点。参看《红线》26-27页。柯嘉豪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讨论也有见地,但他误认为是龟兹王强迫鸠摩罗什与公主发生性关系。
[79]我们必须记住:僧侣佛教史家有决定选用手头哪些材料的自由,而他们选择的标准常常是不同的。例如,在僧祐与慧皎给昙无谶写的传记中,就未涉及任何有关性技巧及破色戒之举的内容——尽管这位大师是以此著称的。相反,这些内容只出现在《魏书》的昙无谶传中,参见《魏书》卷九十九,第 2208-2209页。
[80]尽管中古以后的僧侣佛教史家们将鸠摩罗什的破戒行为归罪于世俗统治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并没有忽视鸠摩罗什在自己的破戒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佛教编年史《佛祖历代通载》的编纂者念常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惋叹道,如果鸠摩罗什的所作所为能与其知识相谐,他的寿命将更长,并将取得远胜于今的巨大成就,《大正藏》:2036:529a10。
[81]《大正藏》:2059:330b23-25;以及《大正藏》:2145:100b24-26。我同意汤用彤的看法,“止”字当为“正”的文本讹误,在这,后者更为清楚地表现出了“仅仅”的意思;而“携诣”当作“俊义”。参看汤用彤校注的《高僧传》卷二,第56页,注第29和30。
[82]塚本善隆认为与这一预言有关的传说可能很早就出现了,并且并合而成了僧祐与慧皎传记中的相关叙述。叙述这一预言的目的是将鸠摩罗什的破戒行为辩称为业报的结果。这当然是可能的,但即使这一观点成立,僧祐和慧皎也均未强调业的因素。参看氏著〈仏教史上における肇论〉,第134页。
[83]《付法藏因缘传》中,商那和修对优波崛多说“佛記於汝在百年後,坐禅第一,大化众生”。见《付法藏因缘传》卷三,《大正藏》:2058:306b11。
[84]有关鸠摩罗什的生卒年问题可参看塚本善隆:〈仏教史上における肇论〉,第130-135 页;鎌田茂雄《中国仏教史》第二卷,第213-226页;以及罗宾逊:《印度与中国的早期中观思想》,第244-246页,注第1。根据据称为僧肇所作的〈鸠摩罗什法师诔〉,鸠摩罗什为吕光所获时,已经超过了三十五岁,《大正藏》:2103:264b20-265b02。然而,这篇诔文中给出的生卒年与僧祐和慧皎的鸠摩罗什传记中提出的有严重冲突。根据这两部传记,吕光认为相对于其声望而言,鸠摩罗什太过年轻。而三十五岁在中古时代则无论如何不能算太过年轻。这篇诔文其实是后人的伪作。塚本善隆是第一个指出其为伪作的人,但他根据的主要是外部证据,比如此文在七世纪道宣编的《广弘明集》里才出现。塚本善隆提出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但还远不足以作出最后的判断。因为这篇诔文的确看上去是以接近僧肇时代的文章风格写成的,所以伯希和,诺贝尔以及汤用彤等学者都认为它提供的时间是可信的。参看伯希和:〈鸠摩罗什研究札记〉,第16-17页,诺贝尔:〈鸠摩罗什〉,第228-229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04页。但我本人也认为这篇诔文必为伪造无疑,其证据来自文章本身的表达。最明显的破绽是文章里的“大秦苻姚二天王, 师旅以迎之”(《大正藏》:2103:264b20)这一句话。众所周知,姚兴的父亲姚苌篡位并谋杀了前秦的苻坚,从而建立了他自己的朝代。而僧肇所处的时代符坚的残部和后秦政权双方持极度的敌视态度,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魏书》中苻坚、苻丕、苻登和姚苌、姚兴诸人的传,《魏书》卷九十五,第 2076-2082页;《晋书》卷一一四至一一六。很难想像僧肇会在诔文中冒着冒犯姚兴的危险来称颂苻坚,而且将两人并提。所以可以断定这篇诔文所作的时代在僧祐慧皎等的作品出现之后。而其作者虽然熟悉有关鸠摩罗什生平的一些事迹,但对僧肇那一时代的政治禁忌完全没有敏感。最有可能是该文作者就是按照《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记写成这篇诔文的。日本学者斎藤达也在他的一篇近作中也持相似观点,他同时指出诔文中有隐射鸠摩罗什破戒的文字,也不太合情理。参看他的〈鸠摩罗什の没年问题の再検讨〉,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纪要, 3(2000):129-130。
[85]学者们基本同意这一观点,参看鎌田茂雄《中国仏教史》,第一卷,第223-224页;普瑞:《中亚佛教》,第119页。一般认为,优波掘多是说一切有部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秣兔罗建立起了佛教僧院制度,《大正藏》:2043:510c23-156a5。
[86]《大正藏》:2059:334a26-27,2145:102b21-22。
[87]这段话中的“不受师敬”一句话,在有的《高僧传》本子里是“不受师教”。根据上下文,“不受师教”也大致可说得通,可以指鸠摩罗什自知犯戒,所以不能传授(“受”即“授”也)卑摩罗叉(师)所教(即律)。但是卑摩罗叉问的是鸠摩罗什有多少弟子,所以如果鸠摩罗什回答仅仅讲他自己传法而不传律,那就显得文不对题。所以显然应该是“不受师敬”。
[88]《大正藏》:2059:332c17-21,2145:101c28-102a03。
[89]佛雷:《红线》, 第96, 98-143页。
[90]根据现存资料,我们无法确定在凉州期间,鸠摩罗什是否被禁止传教。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此期间他曾从事过佛教信仰方面的活动,但据《高僧传》〈僧肇传〉,僧肇就是在鸠摩罗什到达姑臧(即凉州)时前去投他为师的,见《大正藏》:2059:365a19。
编辑:李纯一
来源:《中国学术》2006年第2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