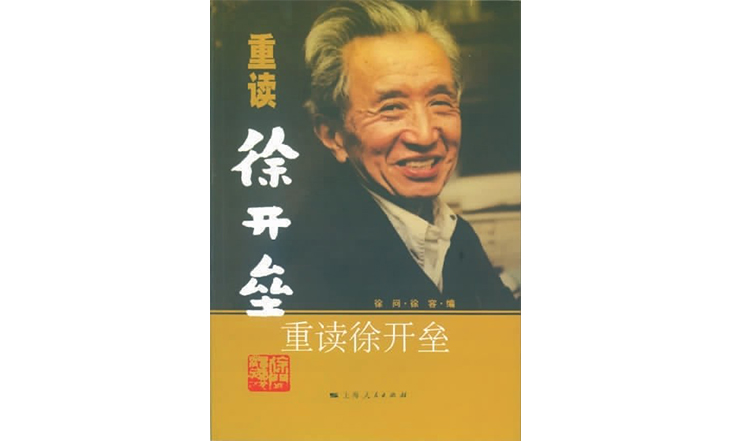
五泄瀑声贯耳,反倒显得周遭特别的宁静。透过一幕幕水帘,眼前一派空濛。我端坐在池边桥旁的皱石上,虽是初冬暖日,久坐仍生寒意。同样是作协散文组采风于此,前一次是在1991年,同样在这堆石墩上,我同开垒先生的一张四人合影就在此定格。记得那天先生笑问:你编副刊也有十年多了吧,应该也算老编辑了。我调皮地回答:我这个小编辑是你这个大编辑“编辑”出来的。可能接近梓里,他的话更多,普通话里的宁波口音也愈浓了。一晃26年,先生已作古人,但透过历史的迷雾,他的种种往事、音容笑貌,如同昨日,清晰可触。
1979年,我从团市委调入刚复刊的《青年报》主编“红花”副刊。去找报社的老总编、诗人肖岗请教,他说,他现在《上海文学》编诗歌,这方面可以交流交流,至于讨教,最好去找“笔会”的徐开垒。当时我单身,每天用麻袋装的稿子请几位业余作者帮忙检视完,往往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可到文汇圆明园路开垒先生办公室,他仍精神矍铄,正在挑灯夜战,当时副刊编辑的辛劳无以言表。我也不客气,常常带上些选好的稿件,甚至大样请他指点。他看得认真,有时批评得也厉害。有一次他推荐了一篇青年习作给我,说小说题目没起好,你想想。回去后我电话告诉他:《喜相逢》如何?他电话里沉思一会:也不太好,再想想。过了两天,在付印之前,突然接到电话:小吴,就喜相逢吧,也想不出更好的。
“红花”副刊正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波文学热。在先生倡导下,我们同三大报一起举办了“微型小说命题创作大赛”,从中发现了一批文学苗子。开垒老师对我说,诗歌是属于青年的,在他鼓励下,我们同北京《诗刊》合作举办了全国青年诗歌大赛。1981年底万体馆举办《我们的生活》诗歌朗诵会,他也电话鼓励我:看到朗诵会有你写的诗,很好,你不能光写散文、报告文学,一个编辑最好是个多面手。后来“红花”刊发了上海一位高中生写的《柳眉儿落了》,这种中学生早恋题材在当时是禁区,三个月后《文学报》转载此小说并在全国范围展开讨论。那晚开垒先生在办公室开玩笑:小吴,看不出侬胆子还蛮大额。
当时,卡夫卡、加缪、萨特等名字给文学青年带来了巨大冲击,一些习作往往晦涩极端。我至今仍保留着先生给一位业余作者小唐的长信。稿笺正反写得满满的,主要是对两篇小说的意见:如“我觉得你的两篇作品的共同缺点是选材不理想……编造的成分多,写我们的社会阴暗面,有些使人不能相信真会有这么一些事情”,“要真正深入生活,了解生活,解剖人的灵魂,揭示生活中美和丑的斗争,这才是一条写作的正路”。当时我想发表这封信,被开垒先生婉拒。他说,这是一个编辑应该做的事;除了写信,也应该针对性地找一些有潜力的小青年当面聊聊,效果更好。那晚,我们谈得很多,先生见不得死板的概念,见不得毫无灵性的千篇一律,更见不得灵魂的污浊阴暗,讲到激动时,用食指不断敲击桌面,我深得教益。
严霜结野草,微雨洗高林,五泄对面仿佛始终印着那慈祥的面容。可先生离开我们已逾六年,他儿女新近编撰的《重读徐开垒》 也已面世。对我而言,写作此文是种怀念和敬仰,而且离得越远越能透视时间的深度。开垒老师,我们后辈从您身上也学会了静静地守候着文学的精神家园;学会像您那样走过自己的人生,好比一枚香墨,为后来者“正透焦白,虚心发墨”。
文:吴纪椿
编辑制作:王秋童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