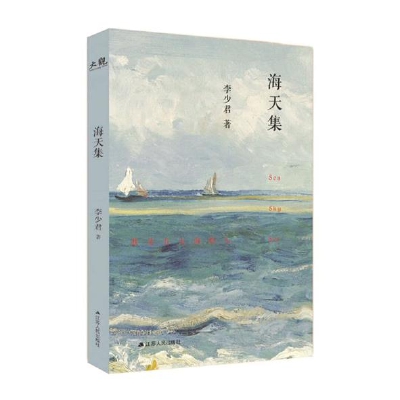
《海天集》李少君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世界与吾心,对于诗人来说是没有边界的。在这里,不得不语及李少君开发的一个反常的句式“我是有某某的人”。这个句式他反复使用,别出心裁,具有令人诧异的转喻之意。或将外视点描绘转为心灵的内视点。如在《我是有故乡的人》一诗中,父亲、少年、东台山与涟水河都可以成为与我同一的视角,从而统摄故乡的过去和现在、人生和时代,将具有历史感的存在纳于我心,笔墨之重,颇具沧桑之感。或借之实现与时代的同化,将庞杂的历史言说化为清晰简约的个人言说。如在《我是有大海的人》一诗中即是如此,诗人将海南特区的整个历史进程内化为“我”的叙述,我即海南,海南即我,使历史叙述完全隐匿于个人化的叙述之中。又或将内心的哲思投影于一个客观事物。如在《我是有背景的人》一诗中,诗人以虚幻的云雾为心境之物。
我是有背景的人
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
三三两两,影影绰绰
沿着溪水击打卵石一路哗哗奔流的方向
我们走下青山,走入烟火红尘
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
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
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
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
就像塞尚抛弃事物与景色的真实一样,这首诗歌的叙述全在隐约之中。如果直观呈现,沿着溪沟下山,从云雾深处走出来,回到都市生活之中,这一生活场景将予以客观的富于诗意的描写,也就是提供空间图象和人物形象,标示清楚的景物,表明关联人物。但是,一切潜隐不露。因为这首诗歌的侧重,不在观察呈现,而在隐喻:
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
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
在这首诗中,云雾才是诗人心灵聚焦之物,这个意象成了自我与世界之间一件新奇的薄纱。即使回归了城市,云雾依然在场,只是这时候它已不再是客观之物,而是感应之物。它叠加在我们记忆之上,散布在生活之中。说实话,云雾的意象在当代诗歌中俯仰皆是,可是像这样给人以陌生化效果的,还真没读到过。
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
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
诗句的进展使云雾进而与生存意识共存,与生命的本质同化,甚至成了生命中最独一无二的超然意识,照亮我们存在的深度。
如果说李少君的诗歌《抒怀》的世界观是处世宁静的话,那么在《我是有背景的人》中,他注入的生命体验意识是超越。他以云雾为意象,在哲思上传达了虚空而无限的古典情怀,传达了历史的在场。从这样的角度,不难理解诗人所谓的“背景”,乃是历史的范式,积淀于我们内心的人文精神与独立人格。
换言之,在传统的烛照下,无限与超越,也是诗人对自己在艺术法则创新上提出的一个信条。纵观写作之路,每个人都在乘筏,舍筏,登岸,经历反复的过程。美国诗人庞德的写作座右铭是:日日新。路漫漫其修远兮,超越,对于技艺孜孜以求的李少君而言,自是不言而喻。特别在诗歌容纳世界的意识上,他曾经这样说:“有清晰的自我判断和历史意识,是优秀诗人的重要禀赋。”显然,诗人已经知觉到今天写作的一个困境:历史与时代这样的视野在诗人眼中隐匿或者说忽略了。一味地将博大的沉思域抹除,诗歌愈来愈矮化,甚至残废,同样是陷入了另一个窠臼。
世界的格局无穷,事实上,诗人可以写作任何东西,只要你有高度的时代感、高度的生命觉察力。
谈论史诗,我知道,不少人有着针锋相对的观念,以为乱弹调子,或觉得很笨。其实,诗歌写作本身就是笨事,但这“笨”也许正是诗的伟大奇妙之一。换言之,诗歌从来就不会仅仅是精致的轻体诗,或者小喜剧的段子诗,它从来就是一个民族最细微也最壮阔的生存经验与精神感受。在文化传统上,中国诗歌史诗的实践从未停止,杜甫、元稹、白居易、吴伟业这样的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在国外,不论是诗人沃尔科特、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还是小说家品钦、多克托罗、波拉尼奥,这个名单也可以无限延长。因而,宏大与个人化叙述从来就不矛盾,诗歌可以也应该具有它历史意识的宽广领土,好的诗人也应该是那些容纳无限世界、拥有无限意识的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诗的创造力永无止境。如同我们不可能人人登陆月球,但照样可以写一首登陆月球的诗;如同荒漠渺不可知,但它对人类的心灵并非没有吸引力。
不言自明,海与天也罢,荒漠也罢,它们都具有不可测量的空间形态,即使身处寂静、孤独的荒漠中央,也不失奇迹的存在,这是诗人容纳世界的博大意识。世界无限,时代与历史的存在也是如此,它在我们心中存在,等待着我们的想象力加以支配,等待着我们用语言重建世界,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匆匆走过。正如李少君在诗篇《荒漠上的奇迹》中所隐喻的:
荒漠上还有一些奇迹
是你,一个偶尔路过的人创造的……
在这首诗里,如果细读的话,我们可以读出哲学,读出历史,读出预言,读出一个诗人对于未来的期待。
作者:谢君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周怡倩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