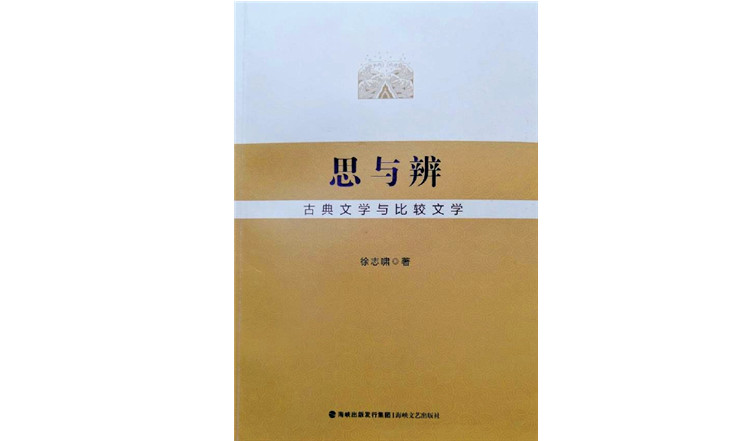
▲《思与辨》
徐志啸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位学者的学术研究,当然离不开思考与辨析。或者说,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就是思考与辨析的过程。徐志啸教授是一位楚辞研究专家,又是一位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是跨界研究的学者。在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无论是楚辞还是比较文学,都可以看到他深邃的思考与睿智的辨析。这一次,徐志啸特地摭取其部分未集结的论文结集出版,内容包括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定名为《思与辨》,正体现他跨界研究的“思”与“辨”,在交融中思考,在辨析中协奏,在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不同领域演出一曲交响的协奏曲。
在“古典文学”部分,作为楚辞研究专家,徐志啸不再只论楚辞,而是将焦点投射到更加深广的领域。如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思考,对于中国文学起源的探索。在《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与思考》中,作者指出《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许多特点,包括其编写者“努力写成文学文化史”的意图、文学史的分期、入选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印刷与文学传播的关系,甚至中国文学史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等论述。这既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显著长处,也是国内众多文学史著作的短板。作者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评析,体现了比较的眼光;他所揭示的国内文学史著作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差异,则体现了作者辨析的思路。聚焦于此,作者有了进一步思考的结果,这就是书中的《科学理性地认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之源的对话》。前者从世界文学的视野范围内对中国文学的观念产生进行了辨析,从概念和理论上说明不能认为文学史在中国古代已经明确并成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文学之源的对话》一文中,他对于中国文学之源“六经”说进行了辨驳,对中国文学之源进行了考察,并以屈原《离骚》的产生来揭示文学的产生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学之源应该是从有人类开始算起,而不应该从有文字算起。”因此,他不赞成“六经是中国文学之源”的结论。
就是讨论楚辞,徐志啸也不再只是论述楚辞的本体,本体之论在他的《楚辞综论》等多部专著里已经有了充分的展现。在《思与辨》里,他要思考的是楚文化与楚史的关系及其对楚辞的影响。关于楚文化,前人已有不少的成果。但是徐志啸探索楚文化的起源,目的是为楚辞研究寻找更加深远的文化背景。他指出,楚国的兴起、楚地的地理气候、楚人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和问鼎中原的霸气,都是产生瑰丽的楚辞的文化条件。对于楚辞研究,徐志啸“采取了将古代文学与比较文学融为一体的做法”,自然地“对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关注和兴趣”。所以,他把视野扩展到东邻日本,对一个世纪间楚辞在日本的传播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详尽总结。
徐志啸的科班出身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正因为有这样扎实的基础,他的比较文学研究,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交融与协奏的特点。他辨析东方诗话与西方诗学的异同,从概念上加以界定与区别。对叶嘉莹先生用西方理论与方法解析中国古代诗词之特点,徐志啸从西方的阐释学、符号学、现象学、新批评、接受美学等理论的原始意义出发,辨析叶嘉莹先生是如何运用这些西方理论对中国古典诗词作怎样的阐析。如指出叶嘉莹认为张惠言对温庭筠《菩萨蛮》词的解说,犯了与西方符号学家一样的弊病,而王国维的感发说词的方式,既有中国传统重视感发的深厚根基,也可以从中找到西方的理论依据,是属于对美学客体的一种哲学解释。这样鞭辟入里的论述,深度体现了徐志啸扎实的两个领域研究的功力。
在“思”与“辨”的协奏中,最能体现徐志啸思辨特点的,是他对于北大版《比较文学概论》存在问题的批评、对“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思辨、对汉学概念的界定。对于北大版《比较文学概论》,徐志啸给予好评,用“创新、严谨、开放”来评定它。但是,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徐志啸还是指出其存在的六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提出者是立论有据的,有的的确是著者明显的逻辑错误。好评和批评同在,体现了一位严谨的学者的学术品格与学术良心。在论述“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是非时,徐志啸质疑了惯常命名“中国文学史”的存在问题以及“华语语系文学”命名的弊病。在对“汉学”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立场。这些,都足以体现其深入思辨的特点。
在《思与辨》一书中,可以发现徐志啸立论,并不先设客观坐标,而是从具体的事例出发,然后得出相关的结论。如细致分析叶嘉莹先生对王国维说词的论析,揭示王国维说词的哲学理念。对《剑桥中国文学史》以文类分割的做法,徐志啸举出其对“赋”体的疏忽以及对东汉“崔氏家族”和“班氏家族”并列的不当加以批评,归纳出“对待欧美的汉学,实在应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应盲从”的结论。书中此类例子甚多,不胜枚举。
作者:郭丹
编辑制作:薛伟平
责任编辑:周怡倩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