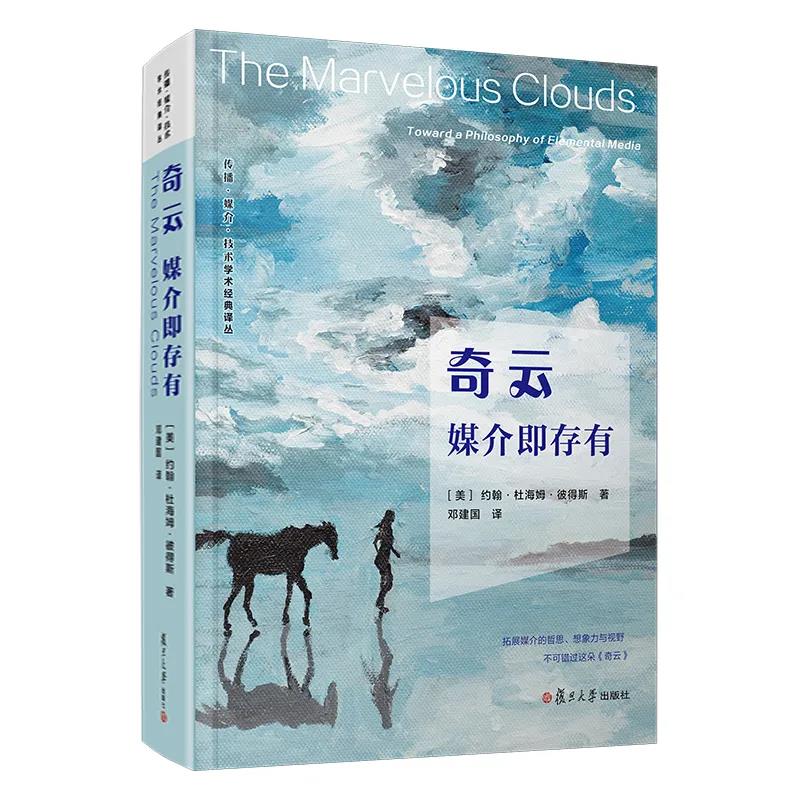
《奇云:媒介即存有》
[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著
邓建国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何谓云之奇?似有似无,亦真亦幻,难以名状。
何以知云之奇?可以用眼看(身体),可以用笔画(技艺),可以用望远镜观测(技术)。若无眼睛、画笔、望远镜,便不知云之奇。有了它们,关于奇云的描述与记录,汇聚成文化之河,流经时空。
彼得斯问道:若无船舶,海洋是否依旧神秘?若无火种,自然是否依然狂暴?若无时钟与历法,时间该如何感知?若无书写,人类是否依然蒙昧……他往来于古今中外,穿梭于学科之林,用现代科学解答古老谜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为何?
若无天问,难有奇云。
凭一己之力,跨十数学科,彼得斯的思想实验最终凝聚成这本《奇云》,贯穿着一条中心线索——无媒介,不存在;真意却在言外:人类若能超越媒介,便超越了自身。
看透媒介,绕不开这本《奇云》。不要用力读它,让它向你舒缓绽放,如立于高山之巅,看云海翻涌,必有所悟。
>>>>精彩书摘<<<<
人类一直都需要某种帮助。
——F·W·J.谢林
媒介非表意,媒介即存有
在其精彩的回忆录《一个关于爱与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中,阿莫斯·奥兹(Amos Oz)有这么一段回忆: 从1930年到1940年代初,他的父母居住在耶路撒冷,那时他的父母会定期拨通长途电话,问候他们居住在特拉维夫的亲戚。这样的问候每隔三四个月会发生一次,每次双方事先都会通过写信来约定好通话的具体时间。
做好约定后,双方都会数着日子作漫长的等待,然后在约定时间用付费电话拨通对方的号码。“这时在药店,电话会突然想起,铃声总是让人兴奋,那一刻真是让人觉得神奇。”在日积月累的兴奋到达高潮时,双方的对话是这样的:“有什么新消息吗?很好。嗯,那我们又会很快通话的。很高兴听到你的消息。我也很高兴听到你的消息。我们再写信约下一次通话的时间吧。我们还会再通话的。是的,一定会的。会很快的。下次再见。好好照顾自己。祝你一切顺利。你也是。”
然后,他们都挂断电话回到靠写信安排下一次通话的常规生活,而下一次通话通常要到几个月之后。奥兹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搞笑叙述者,在此他的幽默是通过一个“还未开头便煞了尾”的对话来展现的。但是,通过一系列通话来讨论安排下一次通话,这并不只是一个具有荒诞意味的周而复始。奥兹的父母和亲戚打电话的目的并不是要交换什么新闻,而是有着更加原初(primal)的目的——听到对方的声音以确认对方仍然活着并存在于真实的时间里。他们所做的就如同那蝉虫,有的在地下潜伏了17年后才爬出地面开始鸣叫和繁殖,然后又进入新的生命轮回。他们的每次通话都小心翼翼,以免它成为最后一次,每次通话中的“会很快的”都是一次表达希望的行为。
电话被称为生命线,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尤其突出: 那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命运以及整个欧洲的命运都命悬一线。当时也只有少数人预见到了欧洲后来发生的可怕情况。
奥兹的亲人们通过信息与传播技术基础设施所交换的是各种有关“在场”的符号。他们的通话行为中所蕴含的意义是存在(existential)层面上的,而不是信息(informational)层面上的。通话双方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可谈,却在交换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以上例子意味着,我们可以将传播视为传者发出的存有性话语(discourse of being),而不仅仅是其对清晰讯号的追求,由此我们可以将“媒介”(medium)这个词解放出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海洋、火、星系、云朵、书籍及互联网这样的媒介(即使我们弄不清它们意味着什么)都深刻地锚系着我们的存有。整个自然界——最终极的基础设施——对我们而言是如此,我们的身体亦然。维特根斯坦曾说,在数学中,一切都是算法,没有什么是意义。
他也许会同样地评价媒介、音乐和其他一切重要之物。
所有媒介都非表意,它们本身即存有。
奥兹的亲人们通过写信和电话保持联系首先是为了维护着他们的关系生态,其次才是为了互通消息。在人与人之间,各种媒介都在扮演着“元素型角色”。只有我们在将传播(交流)不只理解为讯息发送时——当然发送讯息是媒介极为重要的功能——也将其视作为使用者创造的生存条件(conditions for existence)时,媒介(media)就不再仅仅是演播室、广播站、讯息和频道,同时也成了基础设施和生命形态。
这一物质的和环境视角的媒介观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近年来媒介概念会从“讯息”层面拓展到“栖居”(habitats)层面。媒介不仅对那些关心文化和舆论的学者或公民而言很重要,对每一个会呼吸、会用双腿站立、会在记忆海洋里巡游的人都很重要。
媒介是我们“存有”的基础设施,是我们行动和存有的栖居之地和凭借之物。这一视角使得媒介具有了生态的、伦理的和存有层面上的意义。没有什么事物能比海洋、天空和一个陌生人的在场更令人觉得奇妙了,而此前的大部分媒介哲学却只是从它们前面蜻蜓点水,匆匆掠过。查尔斯·哈茨霍恩(Charles Hartshorne)说,鸟儿们鸣叫不仅因为它们要保护自己的领地或吸引配偶,而且因为自然进化已经赋予了鸟儿对鸣叫的一种热爱,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鸣叫已经成为鸟儿奋力保持身心健康以便存活下去的方式之一——这正是进化的本质。
在某种层次上讲,自我表达和自我存有是相互融合的。我在本章中将深入探讨以上对媒介概念的重新思考及其背后的思想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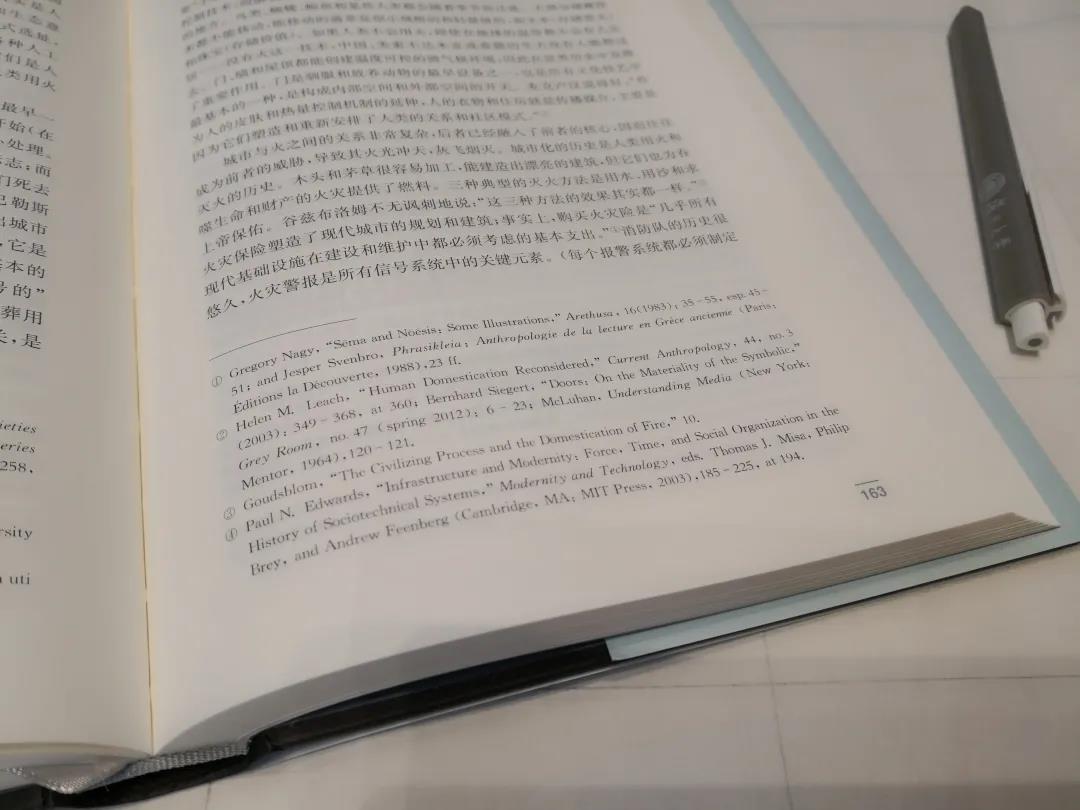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John Durham Peters),美国当代媒介史家、传播理论家和传播哲学家,国际传播学会(ICA)会士,有“美国传播学界的稀有动物”之称,具有崇高声望。彼得斯为斯坦福大学传播学博士(1986),现为耶鲁大学英语、电影和媒介研究教授。著有《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1999)、《取悦深渊:自由言说与自由传统》(2005)、《奇云:媒介即存有》(2015)、《撒播知识:历史中的信息、图像和真理》(2020)。
译者介绍:
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传播学系主任、传播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译著包括《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等。在邓建国眼中,彼得斯是一位稀有动物,一位诗人气质的媒介哲学家。他看上去低调内敛,其实,他不仅悟性极高,思想深邃,而且知识丰盛,文字隽永。这些气质在《奇云》一书中展现无遗。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来源:《奇云:媒介即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