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冬,周末,夜晚,大夏书店里的一场讲座,仍然座无虚席。讲座的主题是阅读,但是很大程度上,听众是冲着两位主讲人而来:毛尖和袁筱一。她们是学者,是作家,是翻译家,也是当下为数不多的、能够让人真正对阅读这件事心驰神往的人。
讲座从袁筱一新近出版的著作《文字传奇》开始。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在讲座之后对内容进行了认真的修订。 ——编者
袁筱一:
《文字传奇》源于我十年前开的一门课,初衷就是想和大家分享阅读的热情。当时也确实投入了很大的激情:阅读的激情,写作的激情。因为年轻,激情里还有很多天真烂漫的成分,有一种对阅读的一往情深,有对讲授作家的一往情深。
回过头去看,这种热情有点盲目,甚至有一些片面,因为是情感主导而不是理智主导的。换作今天,这样的天真烂漫可能会不复存在。原因有两个:一是年龄的缘故,不再那么一厢情愿;另一个是今天的阅读环境也改变了很多。大家对20世纪法国文学的了解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了。
当然,我们可以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这九位作家代表法国20世纪写作吗?我今天的回答是,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代表,虽然不能涵盖;除去诗歌、戏剧,至少也是可以大部分地代表20世纪前半叶的法国小说。
19世纪末,法国文学高唱危机和死亡,但今天走过了20世纪,我们会发现,法国文学不仅没有死亡,而且法国20世纪文学很丰富,有很多和19世纪一样伟大的作家为法国文学或者是法语文学带去了非常多样的写作方式。
而《文字传奇》首先就是想让大家阅读到多样的、有别于19世纪法国文学的写作方式。
毛尖:
很喜欢被袁筱一收到书里的这些作家,而且涉及到的几部作品我居然都看过。从萨特到波伏娃,到加缪,到杜拉斯,到罗兰·巴特,到《流浪的星星》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个不是说我的阅读量有多大,而是我们这一代的阅读有很大的相似性。表面上,在狂悖的青春期,我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法国文学,也许事情的本质是,一半的法国文学天然地适合青春期。

所以,读《文字传奇》很像是一种阅读检索,一次青春的考古学,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把自己的青春期又再回想了一遍,不是岁月乡愁,是蒙太奇般地剪辑了一下自己的阅读史。
回头看,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阶段,大概是阅读量最大的时期,其中中学阶段又更兽猛些,因为那时候在读金庸。不舍昼夜读,披星戴月读,现在有身体写作,那时是身体阅读,一本《笑傲江湖》在家里待一个晚上,第二天还给别人的时候,一家四口接力般都读过了。
后来读大学,图书馆里还会邂逅很多金庸,这些被反复阅读过的书,常常新的时候是两厘米厚,成千上万遍地被阅读后,变成了三厘米厚。

我自己已经不太能回溯,为什么大学里读了那么多法国文学。我的专业其实是英国文学,怎么会对法国文学倾注了那么大的热情?可能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法国更是一种文艺的颓废的象征,法文也比英文更小众,而年轻人自然会觉得小众更厉害些。
整个大学一直到博士,看了非常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然后盗版出来了,主场转换,一直到今天,手机阅读终于把我们都变成零零碎碎的人。所以,现在遇到有人让我开书单,我偶尔会开,以前我觉得书单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手机时代,书单显示出系统的必要性。尤其对年轻的学生而言,他们看了狄更斯,不太愿意往上去追奥斯丁、莎士比亚,而是下沉到网络“狄更四”“狄更五”。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这样,金庸看完看《庆余年》,似乎也觉得是新浪潮新文本。就此而言,书单大概会有点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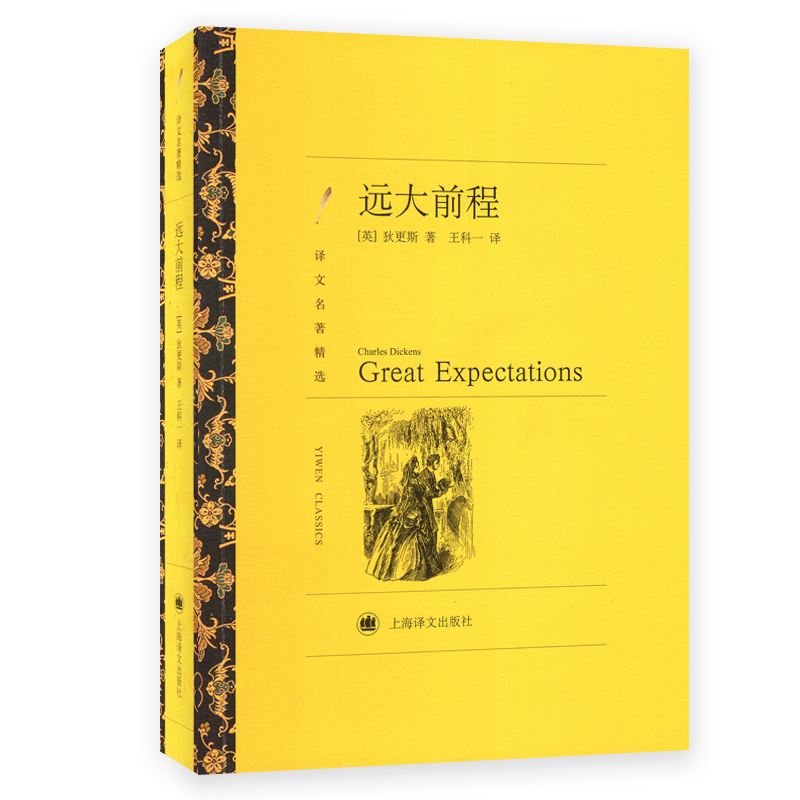
而这本《文字传奇》,就是为我们这个文字已经不再是传奇的时代准备的。就像我自己,每年都会重读奥斯丁,重读几本莎士比亚。尤其这些年,一直因为要写影视剧评论而看了很多烂片烂剧,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粗鄙了,这个时候,跟着《文字传奇》,重新格式化一下自己的胃口和视野,就很有必要。
袁筱一:
年轻时代的阅读和自己后来的成长的确有很大的关系。我在大学里面读到最感动我的原文文本是杜拉斯的《情人》。
杜拉斯毫无疑问是法国最伟大的20世纪女性作家,至少是之一。当时吸引我的当然是《情人》的书名本身,但是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读完之后,竟然没有找到爱情,什么都读到了,就是没有爱情。所以这就是杜拉斯的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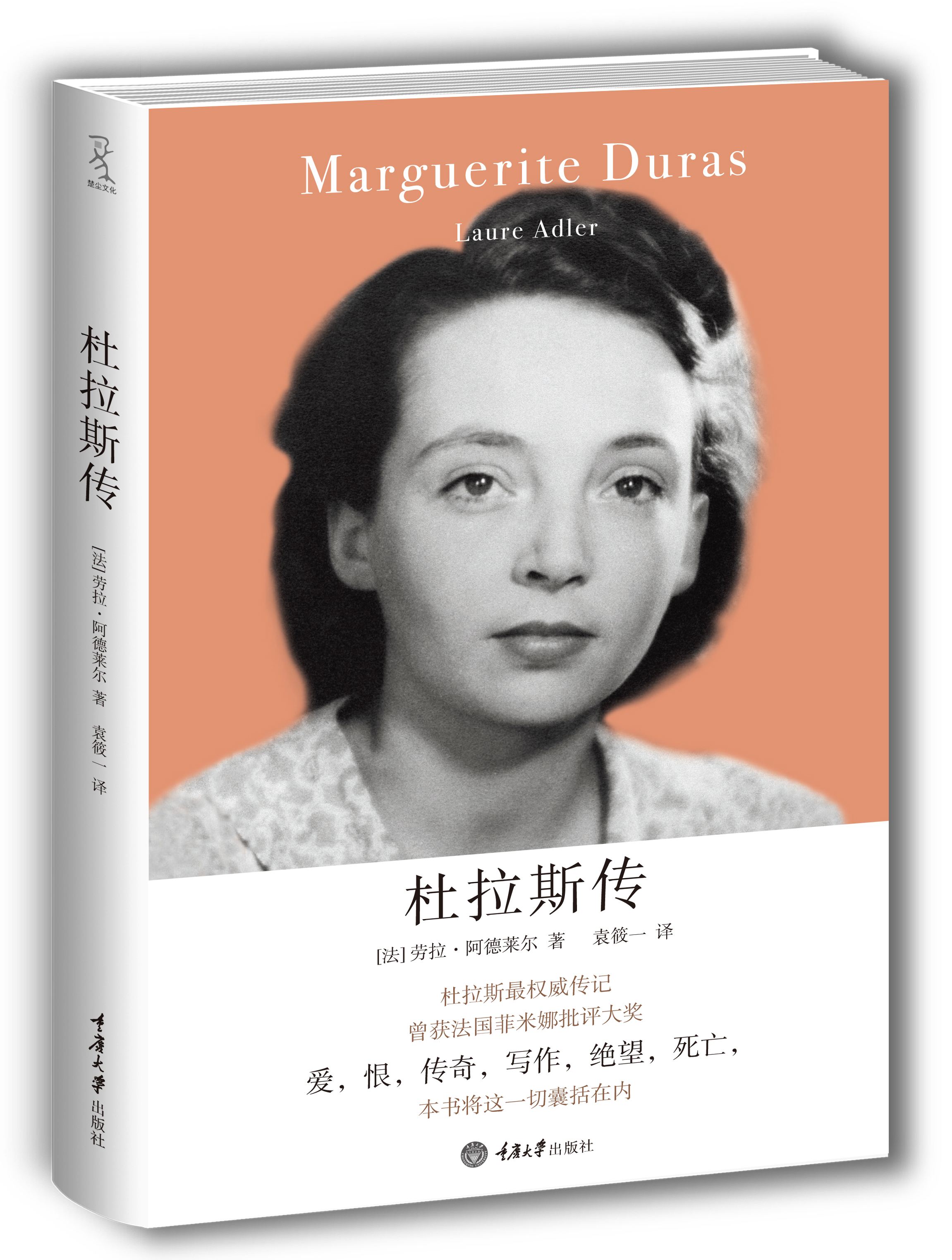
今天固然想撇清和它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承认是撇不清的。我想说的是,它给了我很深的刺激,不是主题上的刺激,所谓一个中国男人和法国小女孩的故事。而是写作方式的刺激,也是表达自我的方式。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原来写作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进行。
那个时候原文书并不是很多,尤其是当代的作品。我记得那本书是法国朋友寄给我的。后来很多法国朋友知道我的20世纪文学启蒙于杜拉斯,也知道我做翻译,他们问我杜拉斯好不好译,因为在法国人看来,杜拉斯应该是很难译的,比如她有很多暧昧,这正好和法国传统写作强调的语言精确性是背道而驰的。
可我年轻的时候,初读杜拉斯所留下的印象,却是有一种惺惺相惜,觉得她是这么容易就踏到了你的痛点。我甚至有一种错觉,哪怕不是那么懂法语的人都可以读懂她。这就很神奇了。今天以专业的眼光来看,当然可以从语言上来讲出个其中的子丑寅卯来,但我想,除了杜拉斯自己想要在语言上的革新之外,也还有一种命运上的安排——杜拉斯在中国的命运。

毛尖:
这个有点像简·奥斯丁,你不需要很多词汇就能读她,我自己就是在中学时候看的奥斯丁,当时觉得似乎也理解了。当然翻译奥斯丁又是另外一回事,看上去那么简易的英文,却怎么也翻不好。所以我一直非常膜拜奥斯丁。我也一直认为奥斯丁可以PK掉世界上所有的女作家。不过这个认知发生在青春期的尾声。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和袁筱一一样,更喜欢萨冈喜欢杜拉斯,因为她们华丽。而奥斯丁不一样,她用非常轻松的方式就为小说确立了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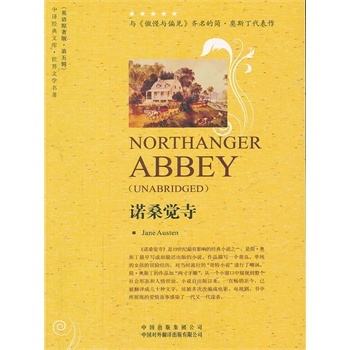
如果说莎士比亚是《圣经》一样的存在,奥斯丁则是散文的莎士比亚。她把莎士比亚的主人公带到了客厅,变成了我们的邻居,有了具体的落脚点和经济位置。她让自然光照进了小说,从此以后,精准成了小说的一个标准,她也因此一劳永逸地把小说带入了一个不再能随便千山万水的时期。
自此,所有的小说都将接受奥斯丁的检阅。而与此同时,奥斯丁还为小说创造了延用至今的语法和桥段,比如,今天我们的影视剧,一半以上还在用《傲慢与偏见》,飞机上的一男一女相遇了,基本是伊丽莎白和达西,这就是伟大的奥斯丁。

不过在我们的青春期,以婚姻为最高浪漫理想的奥斯丁还不能打动我们,我们更喜欢情感充沛的杜拉斯和昆德拉。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快不喜欢昆德拉了。我更爱加缪,用袁筱一写加缪那篇的结尾来说,就是那个,“比萨特沉默一百倍,却热情一百倍的加缪”。
袁筱一:
大学里面的阅读,可能还需要补充一点点。昆德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很红了,他带给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杜拉斯的红则和她的女性身份有关,因为她看起来写情爱,但其实展现了一种巨大的生命力。可她是一个女性作家,于是很多男性羞于承认他们也可以受到杜拉斯影响。很多男性号称他们受不了杜拉斯,说她把一个烂故事颠来倒去地写了无数遍。但是她哪里是在颠来倒去地写一个故事,而是在颠来倒去地玩味文学。
加缪是我蛮晚发现的,蛮晚才喜欢上的,还真的是要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才能懂他。一直到现在,很多学生在读加缪的时候,还会问同样的问题,难道一个人母亲死了不哭就是应该的吗?我们深受浪漫主义影响,所以要把什么问题都要上升到纯伦理的角度。浪漫主义的阅读就是代入式的青春阅读,把自己代入到加缪的《局外人》里当然无法成立。
所以年轻的时候真没办法读加缪。何况加缪背后是一个已然到来的荒谬世界,是哲学思考,是古希腊文学——他大学是读古希腊文学的——的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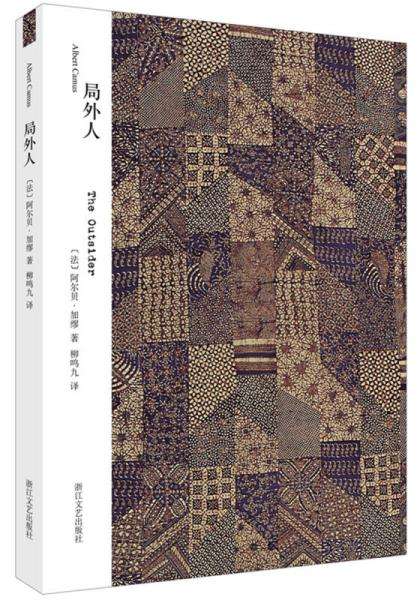
1980年代萨特也很红,但是他的红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并不以小说见长。可他的小说至少比波伏瓦要好很多。另外,萨冈也是一个不错的作者。可能今天我们会有所怀疑,觉得她是我选的九个人中最弱的,今天看来最没有价值的。的确,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很喜欢过萨冈。
毛尖:
但你还是把她放进了书里。
袁筱一:
纪念一下青春吧。只是记录了我们青春阶段中的某一点东西——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忧愁,就是曾经想过背叛全世界,而且拼了一切力气要去背叛全世界。凭借自己的青春就可以藐视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于是只好在小说中得到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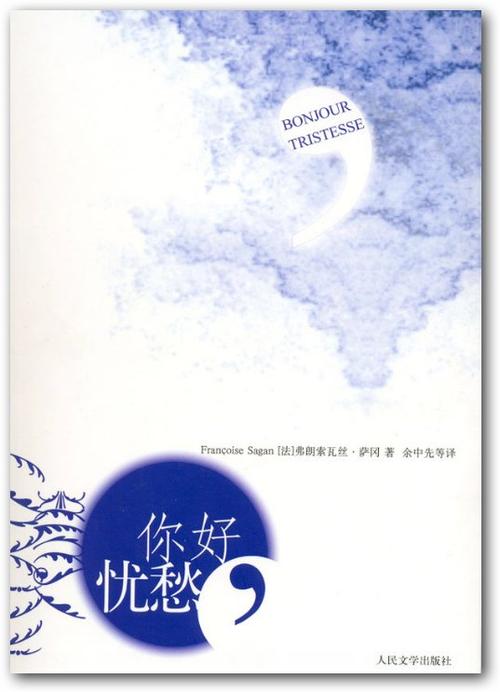
现在我觉得,进入21世纪之后,法国年轻一代的作家明显比萨冈要冷静很多,比如《温柔之歌》的作者。新一代的作家认识世界不需要从认识自我入手,这个和我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我们还年轻,我们也许真的需要通过自我的方式来认识这个世界。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词,就是身体阅读,一定要把自己代入进去,而越是能够代入的是越能够打动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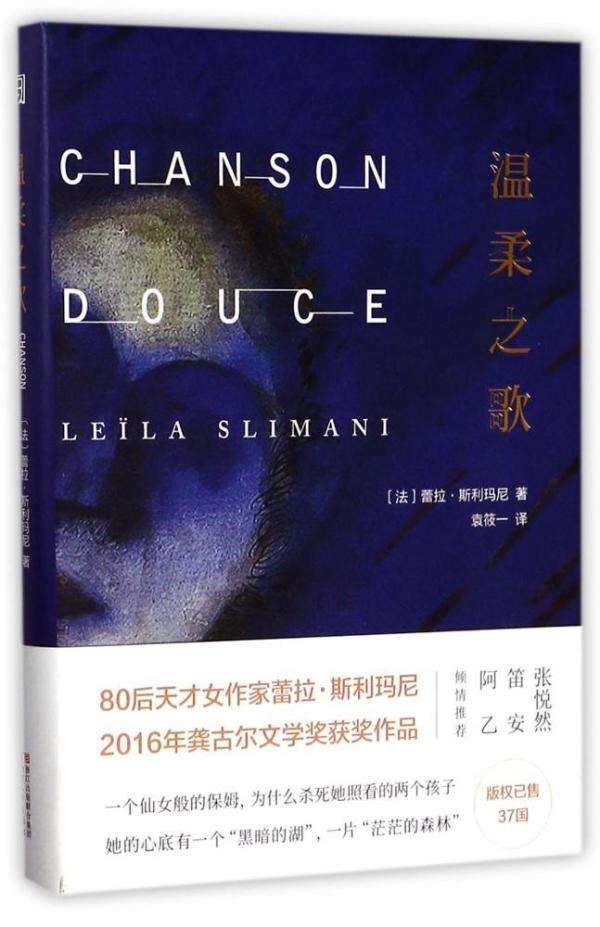
最后谈谈19世纪吧。今天读19世纪,最打动我们的,也许并不是精心设计的情节,说到底,还是对人的关注。包括福楼拜,大家很多人觉得他很冷酷,觉得他的笔下一点像样的人都没有,除了《包法利夫人》中只在最后出了一下场的拉维利里埃尔医生,他好歹忍住了讽刺。剩下的所有人都是可鄙的资产阶级。
但福楼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读完了你才知道,只有对人类命运抱有巨大同情的人,他才能写出《包法利夫人》这样的作品。
据说他倒是并没有说过“我就是包法利夫人”,这句话是他的女笔友杜撰的。不过这里面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承认,他嘲笑的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同类,无关乎男女。既然是我的同类,他所有的弱点就都是我的弱点,是生活在当今社会没有办法改变的弱点。

毛尖: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那时对法国文学的狂热阅读,到底是关乎青春期还是更关乎法国文学本身?是不是法国文学确实有特别浪漫特别与众不同的面向?我们英文系的,晚上不好好讨论《呼啸山庄》,却在那里讨论杜拉斯的名字到底是应该译成杜拉斯还是杜拉。好像那个时候我们都特别能进入法国文学,能和法国文学主人公惺惺相惜。
袁筱一:
20世纪之所以能够吸引包括你在内或者是其他作家在内的一些半专业的或者是专业性的读者,以及大众的读者,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先锋面貌。
其实我觉得法国20世纪文学的姿态还是蛮明显的,展现了和19世纪的决裂。但是决裂是一种姿态,从写作本身来说,也很难说清楚,今天我们再倒回头读一些19世纪的小说,我觉得20世纪的这些法国作家们其实并没有否定掉他们号称要否定掉的东西,以至于在他们的文本当中,仍然将他们要废除的传统不经意地保留了下来。加缪难道不古典吗?

于是,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宣布传统文学的死亡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姿态。但是这种姿态是非常吸引人的,尤其吸引1980年代中国的文学。我总觉得,1980年代中国的文学处在青春期当中,当然会很喜欢这种反叛,很喜欢这种先锋。
但是先锋最大的问题就是,先锋总是在前一秒钟就是先锋,后一秒钟就过时了。其实法国文学20世纪发展到现在,自己也遭遇了困境。当否定了主流和文学的根本价值之后,当文学所有的价值在于形式的时候,形式的探索恰恰难以为继。
其实文学和文化的所有的东西一样,永远是这样的,你看似在永远不断的反叛和吸收外力,但是也会和自己的传统之间形成互动,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回到了原点。
毛尖:
这一秒是先锋,下一秒马上就要遭遇不先锋,这个说法特别好。
有一个例子:超现实主义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他拍的《一条安达鲁狗》可算先锋中的先锋,所以这个电影在影院上映的时候,他很担心下面的观众会不喜欢,就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点小石头,准备在观众嘘他的时候,向他们发出一些必要的回击。没想到电影结束的时候,大家都起立鼓掌,这下布努埃尔真的懵了。没想到先锋的电影,受到了中产阶级的热烈鼓掌,他的内心戏肯定是:这么可怕的电影,难道你们不应该看不懂放声大骂吗!这个结果让布努埃尔很受不了,也深深地怀疑自己的先锋性。

所以,本质上,先锋的本质决定了他们要不断地背叛,包括背叛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年轻的时候,会喜欢先锋,真的是青春期的格式决定的,在那个年代,凡是父母喜欢的,必是我们唾弃的。反是老师提倡的,必是保守的。当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我们也成了被背叛的对象,而回过头看,我们也终于向自己承认,还是觉得雨果更好看,19世纪更好看。一圈杂七杂八下来,还是传统食物最温暖胃口。雨果的描述是那么百科全书那么事无巨细又那么磅礴,光是爱和痛苦,他就千姿百态地描写过,“满桶的火药对于火星,就是怕。”所以,袁老师,再写一本19世纪的吧。当然,19世纪作家的容量都太大,如果再写“十一堂课”,可能需要一百万字。但是,写吧。
袁筱一:
体量大,的确。雨果的《悲惨世界》写了五部,出版社也让他删,他不同意删,他认为删了就是消减了作品的全面性,从而消减了作品的力量。
我现在去读,当然我也怀疑现在的读者可不可以承受这60万字。描写非常铺陈,甚至有时看起来和我们以为19世纪作家最看重的情节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悲惨世界》里面,第二部上来就写滑铁卢,要说和情节有点什么关系,就是为了引出德纳第一家。他花一章的篇幅来写滑铁卢战役,而且是充满了想象的,虚构的一场战争。

巴尔扎克也是一样,作为时代这个历史证人的秘书,巴尔扎克也是不厌其烦地描写一些东西,从衣服的样式到屋子里的摆设。不太符合我们今天的阅读口味,不过他这种不厌其烦的描写,今天的人再也做不到了,我们可能也会有遗憾的吧。
毛尖:
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已经消失,金庸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经常有这个网络作家或那个网络作家被标签为已经超过金庸,但是怎么可能呢?
不过19世纪确实不少百科全书文本,包括麦尔维尔的《白鲸》也是这样的作品,这本书虽然写出来以后没有得到承认,甚至被放入捕鲸类书籍了事,但是, 《白鲸》作为捕鲸类书籍,也完全成立,这是麦尔维尔厉害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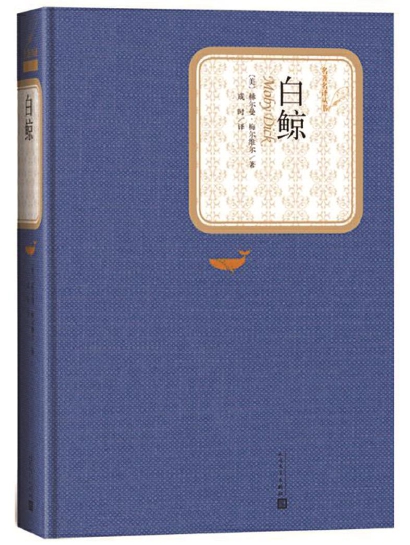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么喜欢看黑帮电影,喜欢看电视剧,是因为,无论是在黑帮还是电视剧里,我们常常还能一瞥总体社会,一种回眸百科全书时代感。这种对总体社会的描述能力,今天的作家大多不胜任了。
对谈嘉宾:
毛尖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
袁筱一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李婷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