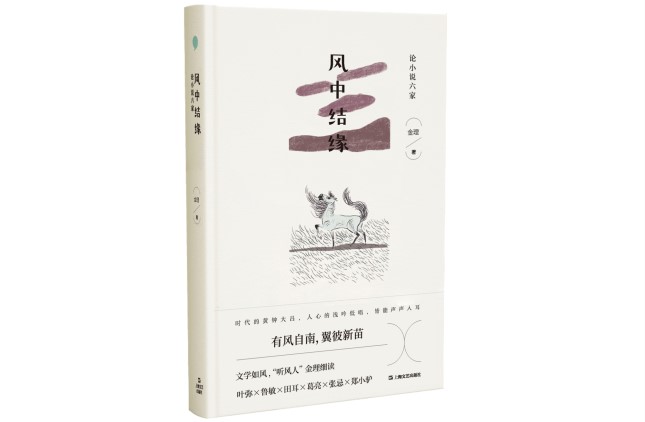
《风中结缘:论小说六家 》
金 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好的文学研究者当是这样一位“听风者”,以作家作品为媒介,而时代的黄钟大吕,人心的浅吟低唱,皆能声声入耳。作家论是金理个人极为钟爱的写作方式,他以求在通读、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研讨叶弥、鲁敏、田耳、葛亮、张忌、郑小驴六位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坛的作家,品味作家文字间的趣味,探寻他们对社会与人心的洞察。
>>内文选读:
小说之心:田耳(节选)
我团着身子,一朵花慢慢展开花瓣。但
我的心没有展开。它紧缩着,如一块秤砣。
它让我安稳地立在冰面上。
桑克的这首诗中,“花瓣的展开”与“心的紧缩”奇特地展示为同一个具有紧张感的过程。田耳的小说犹如这个过程,文本外部的触角探向、卷入纷乱而无限的世界,但同时向内地“紧缩”成“秤砣”般、沉默而“安稳”的心。这个小说之心是什么呢?
拒绝抒情
我从《衣钵》开始记住了田耳这位作家。小说叙述了一场“成长仪式”,道士的儿子李可留在乡里子承父业,情节不复杂,可要将故事讲得入情入理其实不简单。从时潮来说,这是一个都市化的时代,李可的同龄人们攘臂争先地漂往城里;从个人意愿来说,面对群山四合,李可早就有心“离开周遭一切,走出去”。那么到底是什么留下了李可?在村里,人们不知道佛道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区别,做道场的时候,和尚道士一起上阵,“做和尚的做道士的脱了衣便和别人毫无二致地种地养家娶妻生子”。20世纪初叶,在一片拔除宗教、改革陋习的声浪中,鲁迅为田夫野老、蚕妇村氓举办“赛会”、 信奉“神龙”辩护:“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知识分子看不上的、“四不像”的民间宗教活动,实则同农人生活,以及扎根于此生活背后的情感寄托、精神想象有着切身而实在的联系。乡间生活中的生死病痛,“都少不了请道士”,通过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李可领受道士这份职业的意义,且将此意义点点滴滴落实到了一己生命的血肉真实之中。此外,我注意到田耳特别写了李可看月亮的情形,月亮“纠缠的光芒在地上结了一层白茧,给了他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就像在他体内某个最为柔和的地方抚摸他”,他甚至不忍出声,怕“一出声就会弄破整片月光”。同样是看风景,如果和当年路遥笔下高加林看高家村的风景作比照,况味完全不同。其实,“风景”一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过耐人寻味的词义迁变过程,据小川环树先生考证,“风景”最早见于晋文,其初义“本来并非单指目中所见之物而已,还包含有温暖的感觉这层意义”,据《说文》,“景”字本义原是“光”。但中唐以后,“风景”的词义发生变化,“景”字完全失掉了光明的涵义,仅仅成为景象、景致的同义词,当时的诗人们使用“清景”“诗境”“幽景”等词,“这意味着和外界隔绝而自成范围的一个孤立的世界。这里所称的外界就是官场、尘俗的世界。这一群诗人把自己关闭在这孤立的世界里,与此同时,也就不管世间俗务,独来独往,专从大自然挑选自己喜爱的‘景’并以此构筑诗章”。这群关闭在孤立世界里的诗人,可能就是柄谷行人所谓“内在的人”的雏形,也是高加林的先辈;我敢肯定李可不同于此,他站在“风景”的源头,那是一片光明辉映、互相拥抱的“温暖感觉”,那是李可对乡土的热爱与尽责。

田耳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从其天性来说可能也不喜欢强攻创作的单一面向。在我的记忆里,他早年的中短篇,如《衣钵》这样的温暖亮色并不普遍,晦暗、反浪漫、拒绝抒情倒是让读者过目难忘。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像《围猎》中参与“围猎”的那群人一样,无意识中聚拢为群体,赏鉴一幕人性恶的发作。田耳的高超之处在于进一步指出,旁观者也会刹那间转变为受害者,他人即地狱。对于《最简单的道理》中的小丁而言,除了打架的社会青年外,连老师、同学甚至父亲,都意味着暴力和欺骗。更进一步,每个人都面对着整体性的暴力循环,依据即时的强势或弱势地位,扮演施暴者或受害者,比如徐老师在被体育生们揍了一顿之后,转而将内心淤积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发泄到了更为弱小的小丁身上。如何突破这一无尽的暴力循环呢?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自上而下型塑青年人三观的力量早已被瓦解,田耳的小说中也从来不存在含混不清地回返“革命年代”以寻获精神乌托邦或想象性解决的方式。那么本该维护正义和秩序的体制力量呢?考虑到《事情很多的夜晚》中将椅子踹散放火取暖的警察,尤其是《独舞的男孩》中“毛茸茸的警察”追查反标时,那只探向姚姿胸口的、“硬得像一把鞋刷”般的手,你就知道田耳对这样的力量完全不抱信任,他甚至还要在《一个人张灯结彩》的末尾给多行不义的刘副局胸窝子插上一把刀以实现“诗性正义”。当然我们不应忘了老黄,不过他的存在就好似暗夜风中明灭的孤灯,既要和刘副局保持距离,又要时时提醒小蔡等青年警员不走歪路。《最简单的道理》中,从来没有主动伤害别人的只有小丁,他是突破循环的希望吗?在小巷里听到“呼叫的嗓音”时,小丁选择“软软地站着。除了抽自己两三个耳光外,他什么也不能做”。这是一个耻辱的时刻,我想起电影《非常夏日》(路学长,1999)中也有类似桥段:主人公在面临绝境中求助的少女时出于胆怯而无所作为,此后一直忍受自责的煎熬。直到再一次面临生死考验,主人公从被囚的汽车后备厢里赤手拧开螺丝,伸出血肉模糊的手,最终使得自己和少女获救,“完成了以自己的血肉为祭祀品的成长仪式”。《最简单的道理》本也可以视作一部成长小说,但是田耳并没有给出壮烈的自我救赎,结尾处小丁躲在卫生间陶醉地尝试社会青年“教他的那个方法”,完全是一副鲁迅所谓“坐稳了奴隶”的模样。

作者:金 理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