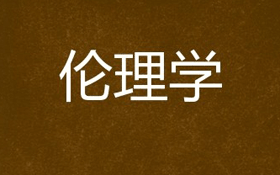
朱贻庭教授的新著《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以下简称《6辨》)是对自己四十余年中国伦理研究成果所作的哲学概括和思考整理。该书旨在通过对中国传统伦理学史的梳理整合、反思总结,深入探讨传统伦理的古今传承与创新,思考其思想资源的现代转化,并试图重建一个具有中华文化“家园”感、又集中体现现代精神文明价值导向的“中国伦理学”逻辑结构和范畴。一个年过八十的学人能有如此的文化担当、学术精神和研究热情,确实是可敬可佩!
观念、思路和方法
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曾引述黑格尔所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阐述自己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观念和思路方法,并以此为指导,着眼于揭示和梳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探索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进而创建了以《智慧说三篇》为代表、真善美统一为核心理念的“中国现代哲学”体系。
朱教授对伦理学、伦理学史的认知和理解,和冯契先生的理念十分相契。他深知,属于哲学范畴的伦理学,自然就是伦理学史的总结,而“中国伦理学”则对应“中国伦理学史”的总结。故他在伦理思想史研究上孜孜以求的是伦理学本身的研究,又在伦理学研究中着力寻找伦理思想史提供的依据和资源。由此塑造并确立自己关于中国伦理学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有三:
首先,他的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不局限于伦理学本身,而是以复合学科的视野和思路,融合哲学的、道德问题的思考,以及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探讨和把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哲学智慧和民族特色。同时又十分注意引入古今、中西辨证比较的研究方法,扩大了研究视野,夯实了学术厚度。
其次,他通过辨析“伦理”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确立起自己的伦理学观,进而阐述“天人之辨”、“心性之辨”、“义利之辨”、“和同之辩”等对偶范畴的道德哲学论题,为构建
中国伦理学的逻辑体系提供了合理的思路和有效方法。诚如他所说:“‘伦理与道德之辨’是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
朱教授审视、剖析了人们混同“伦理”与“道德”的习惯性思维,指出其不足在于由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直接推出“道德”,而不讲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和联系。并指出,这显然是受了前苏联伦理学教科书的影响。
近来,朱教授发表《“伦理”与“道德”之辨》一文(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一期),是对《6辨》一书的增补,将六个对偶范畴扩展为七个对偶范畴。另外,又列举中西方伦理学史上一系列基本事实,系统阐述“伦理”与“道德”的历史辩证法,主张中国伦理学研究要回归伦理学的本质和思想原点,关键在注重人伦关系本身。认为“伦理”规定了“道德”的现实性,而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反思精神”又激发了“伦理”的内在否定性,从而冲破旧的“伦理实体”,通过变革实践的批判与继承,建构起新的伦理关系和新的道德,那就更充实了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体系框架建构的具体内容。
第三,朱教授十分注意将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研究纳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考量,自觉于学理性与时代性结合上,推进中国伦理学的再写与重建。朱教授对于中国优秀文化资源有许多深刻分析和精辟见解,最终归结为思考和回答传统文化“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是应当”这三个问题。他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的思维模式和学科分类,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哲人往往据于义理、辞章、训诂、经世之学,将此种种熔于一炉的特点,善于容纳哲学、伦理、道德于“义理之学”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以更好揭示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建构特点和精神特质。朱教授强调:“不参透中国古代哲人论述‘伦理’、‘道德’的运思方式,不领会中国古代哲人以‘情为基础、情理交融’的道德认知方式,而只是以西方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为‘尺度’,从传统伦理思想中去发现某种合乎西方伦理学规范的那些理论”,那“也就抹杀了中国伦理学的民族特点。”(《6辨》跋)
源原之辨
“源原之辨”是朱教授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对偶范畴。其学理意义在于概括了中国伦理思想古今演变中的传承、转化和创新的规律,是传统伦理思想资源能在传承中实现转化发展,以致现代创新的依据和关键。
所谓“源”,包括渊源与资源两方面,与共时性相联系的源头性的因素,以及历时性意义上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思想资源;“原”,即本原、根基,指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状况及其变革。源原之辨,不同于源流之辨、古今之辨。文化史上的源流关系、古今关系,大都限于文化的历时性、流变性,看重的是文化思想资源的前后演变和联结,忽视其客观的条件和根据。朱教授强调:“源原之辨,概括了文化流变的动因(‘原’),因而跳出了‘传统’本身,立足于现实这个‘原’,揭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建构得以创立的综合成因,即‘原’‘源’整合。”(第7页)
为了进一步辨清“源原之辨”,回答中国伦理思想演变、转化的内在根据和必然逻辑,朱教授主要提出“价值对象性”和“古今通理”两项概念。何谓中国传统伦理中“价值对象性”的存在?《6辨》指出,它是“存在于传统文化资源中,被发现可以为现实社会所需要并可转化为现实价值的价值对象”。这个说法有点拗口,其意是要在传统文化中发掘现实社会文明建设所需要借鉴、采纳的优秀资源,而要使这种传统资源成为满足现代价值重构的要素,则需要通过价值评价来实现其向“现代价值”的转化。
朱教授着重去发现和探讨的不仅是“价值对象性”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和把握“价值对象性”的具体体现和思想表征,这就是所谓“古今通理”。朱教授强调古今之“理”的特质与功能在“通”,认为这个“通”,讲的是沟通之通、交会而通、转化融通,肯定了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伦理思想之间“异”而相通,并视之为伦理思想史上的基本事实和一种发展规律。他还特别指出:“在传统文化中的‘古今通理’,并不等于‘古今同理’”,同时也有别于“古今共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批评诸如朱熹那样的理学家,指出他们崇尚“道统”、专尊“圣贤”、神圣经典,视圣贤经典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完全抹杀了思想传承中的演化和创新,势必导向原教旨主义式思维陷阱。
朱教授指出,“古今通理”不仅是传统伦理所内涵的“价值对象性”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命脉”的特定载体。充分理解和把握传统伦理学中“古今通理”的存在,有助于我们发现、总结古今之“理”相通、承续、转化的基本环节,以实现对“价值对象性”的现代价值再创造。诚如《6辨》中强调的:“因为古今相‘通’故可继承;又因为古今‘不同’,故需要改造和发展。从而实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就是古与今——传统与现实关系的辩证法。”
朱教授还从传统伦理中概括出“贵和”、“重义”、“民本”三项“最重要的价值观”,认为此“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三宝’”。(《6辨》第16页)其特点是将其作为关系范畴(对偶范畴)进行阐述,如讲“重义”,置于义利之辨的思想背景,不仅说清义、利各自的内涵意义,还侧重阐明“见利思义”、“正义谋利”传统思想的现代价值;讲“贵和”,联系“和同之辨”,强调融通、和谐,而非简单归结于“专同”或“混同”,突出“和”的本质是“生”;讲“民本”,则强调“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形态,所谓‘民本’是就君与民相对而说的”,注重的是“民本”对于君主“治国安邦”的重要性,但不应将其类同于现代民主概念。通过这三项样本分析和案例解剖,我们再来看“古今通理”之“理”、“价值对象性”之“对象”,显然就更清晰了。
天人合一
在传统与现代交集、转化的意义上,探究并建构中国伦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其逻辑,是朱教授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使命目标和主要任务。
他既自信自勉,又明确宣示:“要总结积2000多年的由中国古代哲人群体所著成的这部伦理学‘大书’,写好以儒家为主、综合各学派之‘学’,以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概念范畴话语体系为基本骨架的构成古代伦理学体系的‘古典中国伦理学’。”(《6辨》跋)
朱教授确认“天人之辨”才是对中国哲学主要对象的合适表述,而中国哲人关于“天人之辨”的主要观点和思维特点,可归结为“天人合一”。他把这个观点和方法延伸于中国伦理学的研究,着力在“天人合一”的意义上,揭示和阐释中国伦理学的核心理念和理论基石。
朱教授通过比较儒道两家思想,对“天人合一”观念的历史演变做了整体考察和深度解析,概括总结了“天人合一”涵义的两个层面:
一方面,“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人哲学思考的宇宙论,体现为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结构伦理模式,从本体论高度论说人与天地的同构合一,以回答“道(人道)之大原”即“天道”(宇宙)的伦理学(也是道德哲学)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天人合一”的理念还包涵了人生修养的精神境界的设计和规定,以为人生伦理、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和根本途径,就在认知和体悟“天道”、理解和把握宇宙天地之“本真”(根性)。这两个层面的涵义合起来,旨在说明:人文、人道意义上的伦理道德,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也非来自神祇的启示,而是中华民族的先哲圣贤们“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人文信仰。
关于“天人合一”的提法,朱教授虽采用宋理学家张载的概括,似乎偏重于儒家阐发的天人理念,但并不就此归结于儒家。而另外参稽道家,尤其是总结《周易》对于“天人之辨”的思想,认定中国古代哲人的“天人之辨”,实出于《易经》的思维模式,后被《易传》概括为“顺天而应人”的命题。揭示出此种“天人合一”的观念,不是简单地讲天人同一、天人相类,更在于强调人当顺应、敬畏天地,亦能参与天地化育,体现出辩证法的智慧和思维方式,肯定了人与天地“合一”实质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性、能动性的“合一”,用国学大师饶宗颐的说法,也就是“天人互益”。
值得重视的是,据于这种反思性的总结,朱教授还提出“天人合一”作为“宇宙结构伦理模式”的两种类型:一是体现于《周易》思维方式上的天人同构而“相通”,其旨在确立“天”(或“天道”)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教诲和引导人们从内心升起对“人道”的敬重和信念。尽管这不一定是一种科学的理性,但实质上表达的是文化哲学内涵的人文信仰;二是以汉代大儒董仲舒为代表,强调天人同构而“相类”的观念。表面上看,采取了类似宗教神学的表述,然其理论旨趣,“同样是藉‘天道’的神圣性论证‘人道’的必然性与合理性”。(《6辨》第31页)据此,朱教授在归纳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宝”(重义、贵和、民本)的基础上,最近又提出“敬天”理念,认为这也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宝”。
正是对“天人之辨”中涵摄的宇宙结构伦理模式的揭示,朱教授清晰地阐述了中国伦理思想源起、发展的客观基础和立论依据,确认“天人合一”观念为中国伦理学的核心理念和理论基石,显然是据于思想史的事实,又合乎中国伦理发展的内在逻辑的。
* * *
就我的领会和理解,朱教授积数十年之学养和功力,阐发和建构的这个理论体系和话语表述,集中发力于实现中国“古典伦理”与“现代伦理”的连接转化、传承创新。当然,这个“实现”还在进行中,是否最终完成,有待继续努力,接受时代的考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建构这个伦理学体系所据的系列性关系概念,其内涵解析分明,内在连接有序,中国话语特色鲜明。 当然,朱教授的《6辨》及其近著《伦理与道德之辨》,还只是在整体上建构了“古典中国伦理学”的基本框架。其中虽已涉及但未独立展开对“心性之辨”、“理欲之辨”、“人性善恶之辨”等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哲学问题,也未涉及佛学的道德哲学。这就是说,要完成对中国古典伦理学的总结,进而实现再写“中国伦理学”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说朱教授的研究有所贡献,就在于他开启了一条再写“中国伦理学”的路径,发出了再写“中国伦理学”的先声。
作者:施炎平(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