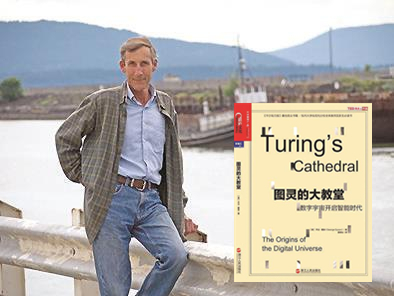
科学史书写者乔治·戴森与其著述《图灵的大教堂》
手艺是沟通的桥梁,却也是壁垒——“真正的惊心动魄之处,并不开放向普通读者”。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价值判断已经呼之欲出:那些“经典”的东西,就应该是慢热的。贝多芬的信里说“困难的东西是好的”。本书一直在强调这样的观点:对复杂东西的认知,是需要艰苦习得才能获取一二的。回报理应缓慢不是吗?深美闳达之处,根本容不下几万人惊鸿一瞥后的点赞。
《星船与大树》是马慧元最新一本散文集(中华书局2018年6月版),也是收入书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现在作者给自己的书起名字,往往是急着向读者剖白,欲从书名中凸显出“自己”。可马慧元不。她笔下《星船与大树》一文的主人公乔治·戴森(George Dyson)也不。
乔治·戴森的父亲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是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小戴森却并没有顺着精英家庭的孩子应该有的模式成长,而是高中辍学,曾经像个野人一样住在树林中,自己造船出海航行,成年之后成为当代科学史最忠实的书写者。个人成长中的故事性实在太强,大可激动人心,然而这些卖座的经历“好像都留给了大海和皮艇,或者自己默默地消化了,没有用它去换来可读可见的成就,甚至没有兴趣让它抵达别的心灵”。
孤寒、辽阔,有一种不肯妥协的天真和骄傲,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最老实的热望。这一切,恰如本书的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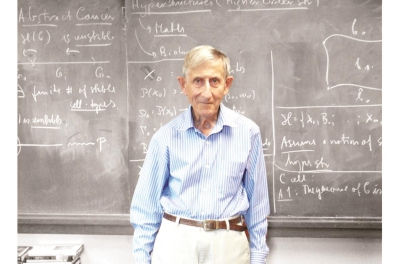
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弗里曼·戴森
马慧元在音乐散文的书写者中算是名人。读者当然还记得她写过的那些人:在漫天风雪中听巴赫的壁炉工人,出去弹琴挣钱回来高高兴兴地经营自己的农场的皮雷斯(Maria Joao Pires),70多岁时手因车祸受了重伤、最后竟然恢复到在卡内基开复出音乐会的西蒙(Abbey Simon)。或许也还记得那些和艰苦的技艺纠缠的故事,“一般来说我花几个月学习一首新作品,先弹给朋友听,再改进一下,然后再小范围地表演,再改进,最终能够公开演奏。这个试验改进的过程一般持续一年,而对贝多芬的作品106号,我花了八年时间”——这是钢琴家陶伯(Robert Taub)写在《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一书中的段落。
而现在呢?
现在是知识付费的时代。
不识谱、不知道古典音乐的惯例和表达规范的听众,想要听上几节课就能懂得钢琴家得练上八年才能把握的细节之浓郁和精妙。
知识付费拉平了世界的距离,边鄙小城的全职太太也能听复旦北大的老师讲课。然而专业的判断本身就是难题。我们爱说“手艺”,现在能判断手艺好坏的人,竟也是极少数了。
我们曾经知道,“知识”和“话语”是一种权力;而现在,贩卖“知识”和“话语”的平台,拥有的权力可能是最巨大的,远远超出“知识”和“话语”本身。他们能与已具备强大变现能力的网红写手合作,也能有办法迅速捧红原本在公众视野之外的书斋学者。
一个被设计的课程,要文化寻根,要洞烛经典;不但有读书乐趣,还能学以致用。
每天30分钟,听众根本不需要为接受某个作品准备好自身储存的上下文,即能享受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你信不信?知识就应该“有趣”和“简单”,学者一辈子苦苦建构的复杂模式,如果听众不能立即“得到”,那就得怪讲课者“没有把话说明白”——你同意不同意?

卢卡斯
马慧元笔下的世界也被这样的需求撕裂着。比如她赞赏的钢琴家卢卡斯(Lukas Geniusas)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其实不缺演出机会,但仍然在尽力参加比赛,展现自己。“我是太贪婪了吗?可是我觉得有必要让人们看见我们……过去我觉得我们应该显得谦虚,但我现在已经改变了想法。哪怕是为艺术,也有必要让公众多多关注。”一方面,艺术家总希望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度;另一方面呢?美国钢琴家库尔茨(Glenn Kurzt)的感受是:给人弹婚礼音乐,立即会感到“骗骗不懂的人真容易”。钢琴家练得死去活来,把所有该受的罪都诚实地受了一遍,最后发现听众根本无所谓,如果努力并不会造成什么区别,那何必不弹点轻松的东西,皆大欢喜?是的,写出《爱乐及谱》,63岁时买一架钢琴来自学,以读谱来济听力之穷,认为需要动用全部的历史和听乐经验去解读古典音乐中的句读的业余爱好者如辛丰年才根本是异数。

罗森
手艺是沟通的桥梁,却也是壁垒——“真正的惊心动魄之处,并不开放向普通读者”。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价值判断已经呼之欲出:那些“经典”的东西,就应该是慢热的。贝多芬的信里说“困难的东西是好的”,而马慧元绝对“不相信连音乐会礼仪也不知晓的观众,能给出令我信服的判断”。她是罗森(Charles Rosen)的粉丝,对罗森的意见都很尊重,表达方式则是老老实实把涉及的谱子都读一遍,希望拥有和他对话的最低基础。世界不是不愿意给优秀者一点奖赏,但毕竟不得不承认:公众的“公平精度”“回报灵敏度”是不能指望的——“你使出140%的力气,都不一定能得到回报,只有积累到某个高不可及的程度,这个愚蠢的世界才惊动了一点点。”本书一直在强调这样的观点:对复杂东西的认知,是需要艰苦习得才能获取一二的。回报理应缓慢不是吗?深美闳达之处,根本容不下几万人惊鸿一瞥后的点赞。
于是特别感动于马慧元的“不势利”。她始终在给你讲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未必闻达,不热衷于在媒体公布轶事,留在维基百科上的痕迹只有作品而无“个人生活”;或许再加一句:名声常常远低于实际水平。

——弗朗克(Caeser Franck)。倾尽全力写了一些歌剧、康塔塔,都不太出名,可是不管有没有声誉,他都可以在琴上自得其乐。直到生命最后一年,为管风琴写的《众赞歌三首》(Trois Chorals)才最终进入主流曲目。

——科迪(Anton Kuerti)。常去大师们不屑一顾的地方演出,主动要很低的演出费,他说太高的费用是会毁灭古典音乐的。某次去了个煤矿小城,仅仅因为那里的一位女士给他写信,说非常想听到你的演出。

——查巴(Király Csaba)。全部演出和大师课都免费。把音栓配置玩得相当透,从小一路拿过能拿的所有奖项,后来同时在钢琴、管风琴上试过能试的所有风格。

——哲学家的早餐俱乐部。1812年左右剑桥的四位“自然哲学家”,在当年的科学界是泰斗级人物,连达尔文发表《进化论》时也渴望了解他们的态度,然而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已经近于被遗忘。其中尤其让人深感命运之手拨弄的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
他出于富家,梦想发明一种辅助计算的机器,生前花费大笔英国财政经费去造差分机,可直到1991年,英国人按照他的设想和当时的工艺水平制造成功,证明设计没错,当年的世界却已经错过了计算机可能带来的改变;他为了制造差分机雇佣工匠克莱门特(Joseph Clement),合作不欢而散,克莱门特却因为这一场合作,意识到工件标准化的重要性,这在未来影响了全世界的制造业。作者感慨说老英雄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然而我们面对的其实一直是一个已经成为定式的世界,惟有钩沉出这样一些阴差阳错的情节,方能时时提醒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敬畏之心:我们看到的“科学发展史”无非是幸存的枝节,浅耨深埋的天才、梦想、与时代的缠斗,不知凡几。
马慧元的管风琴演奏,是能上台演出的水准。她练琴,是那种“不怕否定自己并长期爬坡”的练法。她的写作也是如此,是一种功课:既保持反直觉的训练方式,又秘密收藏着自己的直觉;几乎是小心翼翼地填补着他人叙述中的真空,更又小心翼翼地回避着那些被重复而密集地扫射过的区域。做有难度的事情,成功未必可期。然而唐诺讲过这样的意思:好运气经历得太久太长,会质变成某种正常处境,最终变成你损失不起的东西。于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明明很有才华也很用功的人,在那里重复自己,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阵地。如海明威讲的那样“公众声望日增,作品却往往开始败坏”;而米兰·昆德拉的表达则是:一再重复真没面子。守住“拒绝自我抄袭”这种古典时代做人的基本礼仪,只等待“动态的生长”这件必然会发生的事,真是一种教养。读马慧元的文章,我们知道这样的力量来自哪里。和她喜欢的朱晓玫一样,不在意受众多不多,只“下狠心仔仔细细追摹每个人”。精神长时间集中的难处——和自有其妙处——她收受下来,又弹又读又想,承认进步的途径都是反直觉的,坚信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区别在艰苦中才能凸显,终于“不害怕纯粹是消耗”的可能性,遂能这样一笔一笔写下去。
分享激情与分享思想一样困难。不如留给马慧元自己把话说满:“很难引用书中的大量妙语,因为无论一般性结论,还是针对具体谱例的论述,都太容易脱水而死。”弹管风琴的程序员,一方面致力于沟通而非阻隔,希望能为大众多打开几扇窗;一方面又以自己的阅读经验批评那些为大众写的书“总在可写、好写的地方打转,永远在重复标签或者重组标签”。书写者在进退之际或有胆怯——既坚信真正内核的东西主要是业内的交流,又意识到知识积累被“跨界”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需求——却没有纵容自己的笔滑向平庸、懈怠、固化,只以不一样的节奏,停停走走,写出此时此地、她所经历的这一截时间中的这个世界。
作者:秦蓁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