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维曾在其主编的《教育世界》封面上标榜自己为“哲学专攻者”,显现该时他学术上自我的期许。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学人接触西方哲学的急先锋。然而在滞日期间,当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他语及西洋哲学,王氏“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一直避开这个话题”。王国维对待哲学前后态度迥异,大概因为受罗振玉大力规劝,转而改治经史之学,遂自怼以前所学未醇,甚至烧毁了百余册收集他研读西洋哲学心得的《静安文集》。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国维[《三十自序二》(1907)]
王国维(1877—1927)乃是近代中国学人接触西方哲学的急先锋,他与西方哲学的碰撞,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并且受到甚高的评价[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蔡元培即称赞王氏“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但最后的结局似乎以一场“挫折、误解、追悔”落幕,且从此在他脑海里消声匿迹。果真如此吗?则是拙文所拟探索的谜团。
王国维之所以值得大笔特书,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的青年中有志于外国学问者,无非着眼于自然及实用的学科,在社会科学也仅止于政治与经济学等,而意图研究西洋哲学则属凤毛麟角。其实,王氏对本身学术的定位了然于心,他说:
同治及光绪初年留学欧美者,皆以海军制造为主,其次法律而已,以纯粹科学专其家者,独无所闻。其有哲学兴味如严复氏者,亦只以余力及之,其能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者,吾决其必无也。(《论近年之学术界》)
其自负盖如此。王国维对西方近代哲学,并非浅尝即止,他甚至在其主编的《教育世界》(第129号,1906年7月)的封面上,标榜为“哲学专攻者”,显现该时他学术上自我的期许。而后在滞日期间,当日本学者狩野直喜(1868—1947)与他语及西洋哲学,王氏“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一直避开这个话题”(按:狩野直喜乃是王氏老师藤田丰八在东京大学文科汉学科同学)。相隔未久,为何王氏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变化呢?

藤田丰八◆“王国维之接受兰克史学,盖经由藤田的熏陶。”
首先,必得先厘清王氏“哲学时刻”的起迄点。据《静安文集》的《自序》(1905)云:王氏研究哲学,始于辛丑、壬寅(1901—1902)之间。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追忆之词,恰透露了当时王氏业师藤田丰八(1869—1929)对王国维的期许。他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在上海见着藤田,而后者对其有如是的评价:“头脑极明晰,且擅长日文,英语也很不错,对研究西洋哲学深感兴趣,前途令人瞩目。”但王氏始接触西方哲学,则早于此。缘22岁(1899)王氏至《时务报》工作,并于罗振玉(1866—1940)所创“东文学社”进修,社中日本教师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即田冈岭云,1870—1912)二君故治哲学,因受其启迪。王氏称:一日适见田冈君的文集中有引汗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今译“康德”)、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之哲学者,遂心生喜欢。然而当时王氏自认因文字睽隔,终身无有读二氏之书之日。但在东文学社勤读日文,兼及英文,之后赴日本游学,虽不数月,即因疾告归。但其外语(英文、日文)却愈加精进,成为日后研读西方哲学的利器。
迥异于“新民子”的梁启超(1873—1929)或一心追求“富国强民”的严复(1854—1921),王国维自始即关注人类普遍的境遇与精神状态,诚如他初次(1902)自东瀛归来的供言:之所以从事哲学的原由,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王氏始决于从事于哲学,进入他所谓“独学之时代”。按王氏之谓“独学时代”,乃是意指他脱离正当学制,独自学习摸索之义;因该时读书的指导者犹是藤田氏。所以王氏的哲学探索跨越了“东文学社”及游学日本归来,迄1907年左右。
于王国维悉心追求西方哲学的时段,他不仅刊布了诸多哲学的论述,也旁及教育体制的改革。其故便是:当时清廷鉴于外力日迫,不得已进行教育改革,企图从基础做起救国强民的事业。而该时负责教育大政的执事者,毋论张百熙(1847—1907)的“壬寅学制”(1902)或张之洞(1837—1909)的“癸卯学制”(1903),均将“哲学”一门排除于外,遂引起哲学的爱好者王国维大大的不满。
要之,从晚清学制的设计观来,毋论新制的“壬寅学制”或“癸卯学制”,均本诸“中体西用”的基本精神。当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的“全学纲领”即尤重德育教育,它强调:
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才之始基。
观此,“修身伦理”一门在“壬寅学制”实为德育的首脑。惟此一优势,次年即为守旧的张之洞所压抑。
张氏素重经学,其所主事的“癸卯学制”,以“读经、讲经”作为德育的主帅,而凌驾“伦理”一门。他认为:
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
职是,他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并在大学堂、通儒院加设经学为专科。
尔后,复有官员加入反弹的行列,上疏反对“大学堂”设“伦理学”一门,其所持理由不外:“伦理学专尚空谈,无裨政学实际,复又重金延聘东洋教习,未免糜费;故应予裁撤,以撙节费用,以趋正学。”其间虽有王国维力持异议[王国维曾数次撰文,反对以经学领衔的学制。最著名的为《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却缘人微言轻,无法改变既定的学制(癸卯)。
然而新制的教育体系里,“伦理”一门的位阶容有升降,但其作为学习知识的合法性已渐巩固。按当时甫重议立的京师大学堂,负责统筹全国教育事务,并规划课程。于“中学堂”以上首列“伦理”一门,“中学堂”以下则有“修身”课程。迄“癸卯学制”,“中学堂”以上,则改称“人伦道德”,“中学堂”以降仍维持“修身”之名。
王国维之所以关切教育体制的更革,适与其两度任教通州(1903)和苏州(1904—1906)两地的师范学堂,密切相关。此时复是王氏戮力探索西方哲学的时刻,而他在校担当的课程之中正有“修身”一门。照课纲规定,不外本诸固有儒家的经典,若摘讲陈宏谋(1696—1771)的《五种 遗规》,且应“恪遵经训,阐发要义,万不可稍悖其旨,创为异说”。但王氏却出人意表,挟以西学,融通中外,时创新说,而为学员心悦诚服。加上罗振玉嘱他协办《教育世界》(1902),适时提供了他频频抒发其时探索哲学极方便的平台。
王氏针对该时教育改制独缺“哲学”一事,深致不满,遂诉诸他首发的哲学文章——《哲学辨惑》(1903)。他力辩:哲学非无益之学,并且亟撇清哲学为民权张目的疑虑,以袪除当局的顾忌;况且哲学原为中国固有之学,而中国现时研究哲学有其必要,并倡导以研究西洋哲学弥补中国哲学的不足。因为前者“系统灿然,步伐严整”,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定有所借鉴。这篇初试啼声之作,即为之后1906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所本。后者则明白主张将“理学”(王氏当时权以“理学”称“哲学”)一科直接纳入大学的分科。
其实如前所述,王国维之接触哲学纯系偶然。他与康德哲学四回搏斗的故事,学界早已耳熟能详,最后他系通过叔本华的阐释,方得其要旨。然而于此之前,王氏却不能说全然陌生康德的思想。例如:他业已涉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Baden school)——文特尔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的《哲学史》[《三十自序》(1907)。王氏读的是1901年的英译改本],且迻译过日本康德专家——桑木严翼(1874—1946)的《哲学概论》等,这些文本均有不小篇幅论及康德的哲学。可能情况大约是:王氏固然于康德的论旨略有所悉,但于康德文本本身繁复的论证程序,似一时难以掌握。但整体而言,王氏对德意志观念论的认识,是假道当时日本学界[S.J.Gino K.Piovesana著,江日新译《日本近代哲学思想史》(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第二章至第三章]。要知,日本学界接受德国哲学颇早于中国,其时康德与叔本华思想渐次风行。这恰提供了王国维两位日本老师为何独钟于二氏的背景。
有了上述的时空背景,便能了解他为何在这段时刻撰写了诸多攸关哲学的文本,以及迻译相关的西哲论述,若西额惟克(Henry Sidgw ick,1838—1900)的《西洋伦理学史》(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Ethics,1903刊行)等。要之,评估王国维对西洋哲学的理解,并非拙文的要点;较具意义的是,一窥王氏如何根据他所接受的哲学,运用至其刻意选择的中国文化议题之上。
概言之,康德的“批判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素被视为西方哲学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将原本形上学(metaphysics)奉为一种基本及普遍的论说,转化为一种“认识论”(epistemology)的利器,并超脱传统形上学本体论的形式。这一点王国维深得三昧,例如他曾断言:“汗德憬然于形而上学之不可能,而欲以知识论易形而上学。”(《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在重新阐释及评估传统中国哲学议题,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他取法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先天辩证”(transcendental dialectic)的技巧,解消了传统中国哲学的命题。于是,他特别撷取中国哲学论述最多的三个概念:“性”“理”“命”,予以别出心裁的阐述,而成就了《论性》《释理》《原命》三种不同凡响的文本。在《释理》(1904)一篇,他说:
以“理”为有形而上学之意义者,与《周易》及毕达哥拉斯派以“数”为有形而上学之意义同。自今日视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
在《论性》(1904)文中,他复推衍道:
至执性善性恶之一元论者,当其就性言性时,以性为吾人不可经验之一物故,故皆得而持其说。然欲以之说明经验,或应用于修身之事业,则矛盾即随之而起。
显然他所持的高见,乃系得自康德的教诲——切勿混淆“形上”与“经验”不同范畴的论述。职是他特为表之,使后之学者勿徒为此“无益之议论”[按康德的“先验辩证法”本来的意旨即在揭露传统形上学乃是幻觉的谬思。Cf.P.F.Strawson,The Bounds of Sense: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London:Methuen,1973),p.33.]。这在当时均是石破天惊的立论。惟得一提的,王国维于《三十自序》里,毫不讳言,尝因读《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至“先天分析论”(transcendental analytic),无法卒读,遂得中辍[王国维始读康德之《纯粹理性批判》的日期,他本人的记载略有出入:据《静安文集·自序》(1905),乃是1903年春(癸卯春);然据《三十自序》(1907),则是1904年。个人判断应以1903年春为是,盖原因有二:其一,系年清楚(癸卯),距1905年未远;其二,1904年起,王氏方得陆续刊出攸关康德与叔本华的文章。后得见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赵氏也案语:“《自序》或失之误记。”盖不谋而合也,惟理据则不同]。可是在《论性》等几篇近作,他却能运用自如“先天辩证”的推论,去解析古典中国的哲学命题,其理解康德哲学的功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请注意拙文所用的康德英译本并非王国维阅读的英译本。“transcendental analytic”“先天分析论”(或译“先验分析论”)乃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一部分,而“transcendental dialectic”“先天辩证”(或译“先验辩证”)才是第二部分。循理说,必得先明了“先天分析论”,方能掌握“先天辩证”的妙处。但也有学者认为“先天分析论”才是全书最难理解的]。
此外,在《原命》(1906)一篇,虽然王氏假道康德的议题,但他已能有别于康德,而提出异议,谓“责任”的观念自有其价值,而不必预设“意志自由论”为羽翼。王氏的意见真确与否无关宏旨,但显现了他渐获自信,有所拣择,不复人云亦云了。之后,王氏竟一度认为:之所以读不通康德,乃是康氏其说“不可持处而已”[《三十自序》(1907)]。前后对照,王氏判若两人。

叔本华
进而,他取叔本华的人生观作为立论,阐释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与意义,成为近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先声。甚至,叔氏的思想也渗透进王氏诗词的创作。后者也影响了他对教育的见解。王氏在对德国观念论的追踪下抵尼采(Friedrich W ilhelm N ietzsche,1844—1900)。而叔本华恰巧作为康德至尼采的桥梁。
持平而言,王国维的美学观并非只是照着康德或叔本华依样画葫芦,就中国传统艺术的鉴赏,他提出“古雅”的概念,即有别于二氏 “优美”(beautiful)及“宏 壮”(sublime)的分辨,而深具历史文化意识,委实独具慧眼,卓有见地。
此外,果若王氏的确依循着研读康德,以思索中国文化相关的议题,这段期间他所刊行的代表作,恰恰透露了他阅读的轨迹。例如:《论性》与《释理》之于《纯粹理性批判》;《原命》之于 《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最后,《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一文之于《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它们所涉的议题均呈现了与“三大批判”一一对应的情况。
钱锺书(1910—1998)称誉王氏“论述西方哲学,本色当行,弁冕时辈”。盖非过誉之虚词。王氏攻坚康德哲学,直接苦读康德著作的工夫(王国维除了日文、英文,尚懂德文。他所阅读的康德著作主要为英译本和日译本,但也不能全然排除有参考德文原著的可能。参阅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高山杉《王国维旧藏西方哲学书十种》),自然让他看轻该时梁启超便宜假道日籍,评介康德的泛泛之谈。他不讳言道:“如《新民丛报》中之汗德哲学,其纰缪十且八九也。”(《论近年之学术界》)行文意指梁氏至为显然。尤有进之,他竟致庇议当时翻译名家辜鸿铭(1857—1928)迻译的文本,而讥斥“译者不深于哲学”,遑论深奥的康德哲学尤非其所长[《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1906),20年后,王国维自省“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 哂”]。而康有为(1858—1927)、谭嗣同(1865—1898)功利的政治观与幻穉的形上学,更在他的讥刺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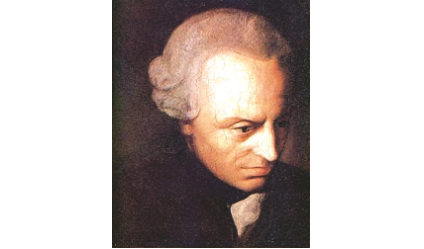
康德“王国维之接触哲学纯系偶然。他与康德哲学四回搏斗的故事,学界早已耳熟能详,最后他系通过叔本华的阐释,方得其要旨。……而叔本华恰巧作为康德至尼采的桥梁。”
于此,王国维心目中的哲学需得略加解析。他执着“纯粹之哲学”,而视其它哲学为杂糅之学。他曾抨击名重一时的严复“所奉为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不解纯粹哲学”,故难登大雅之堂。王氏主张知识之最高满足,必求诸哲学。他拳拳服膺叔本华的理念,谓“人为形上学的动物,而有形上学的需要”。故奉叔本华的形上学为“纯粹哲学”的典范。并以哲学为“无用之学”,方堪与唯美的艺术相比拟,同为人类文化至高的结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职是之故,梁启超和严复辈汲汲于追求经世致用之学,自是为他所不屑。他直言:“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论近年之学术界》,显然此语改造自康德的伦理学的格言:“当视人为目的,不可视为手段。”)而国人“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之者”,且不及千分之一[《教育小言十则》(1907)]。
然而王氏的 《红楼梦评论》虽以叔本华的人生哲学为立论,但在第四章却提出“绝大之疑问”;他质疑叔本华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而于《书叔本华的遗传说后》一文中,复大肆抨击“叔氏之说之不足恃,不特与历史上之事实相反对而已”,且非由“其哲学演绎所得”。其不满之情宣泄无遗。对照早些时他对叔本华思想拟“奉以终身”无比的崇拜(王氏在其1903年9月所作《叔本华像赞》,至谓“公虽云亡,公书则存,愿言千复,奉以终身”),判然两样,此不啻埋下日后告别哲学的伏笔了。
1907年7月,王氏撰有一文,仿若“告别哲学”的前奏。他坦承疲于哲学有时,因为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依王氏所言,所谓“可爱者”,便是“伟大之形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而“可信者”则是“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析言之,在哲学上,便是德意志观念论(Idealism)与英国经验论(Empiricism)的对垒,而王国维的思维恰巧拉扯在二者之间。他不讳言自己酷嗜乃是前者,但求其可信者则在后者。他坦承“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乃是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王国维复对近年西方哲学的发展感到失望,他举德国芬德 (W.Wundt,1832—1920)和英国的斯宾赛尔(H.Spencer,1820—1903)为例,“但集科学之成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虽谓“哲学家”,实则“哲学史家”罢了。循此,王氏忖度,以个人的才性和努力至多也只能成就一个“哲学史家”,而“哲学家”则不能,是故颇觉沮丧。可是他犹未绝望[《三十自序二》(1907),王国维自我的评估却不幸成为之后中国哲学发展的预言。贺麟即说,近50年中国哲学的发展非原创性的哲学。参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又,蔡元培《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
要之,王氏自觉个人的禀性“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显然自相矛盾。他虽有如是自我的反思,但犹未绝情于哲学和文学。依其1907年7月《三十自序》的文末,王氏犹抱一丝的寄望,祈求老天赐予“深湛之思,创造之力”,俾便“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之一日乎”。观此,王氏尚亟盼求得两全其美。因是于诗词的创作之余,他拟从事第四次,也是最后一回攻读康德哲学。
有趣的是,当王国维徬徨于“哲学”与“文学”两条分歧的叉路时,结果他并未像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荒芜之路[罗伯特·弗罗斯特《未曾走过的路》(The Road not Taken)],而是另辟蹊径,以供日后他人追踵的坦途——经史研究。
原来事情的发展,并未从王氏所愿。真正对哲学的致命一击与意向的骤变,尚俟罗振玉的介入与劝导。然由攻读西洋哲学跳跃至罗氏建议的经史研究,王氏尚有一段文学创作的过渡时期穿梭其间。本来王氏每逢苦闷之际,便以作诗填词排遣胸怀,为此,他个人颇感自得。惟后人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评价容或不一。但于其文学研究的成果,却众口一词,交相称誉。盖王氏创作之外,依然不改其学者习性,勤于搜集前人所忽略的素材,经考察、爬梳、阐释文学史为人所忽视的文类。前后撰成《人间词话》(1908)和《宋元戏曲史》(1913)两部开山之作。《人间词话》别开生面,抛出“境界说”,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独特的新视野,令人一新耳目;《宋元戏曲史》则披荆斩棘,探索前人未曾走过的处女地。二者均掷地有声,影响深远。惟一旦他移情专注经史研究,便绝口不复谈此艺。一若它时放弃西学般,便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其骤变、斩决的态度如是。
必须点出的,沉浸西学时刻的王国维,他取径西学所引发的立论,动辄与固有思想有所出入,举凡他所引述的思想——“哲学乃无用之学”,之于儒家“淑世有为”(《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文学乃游戏的事业”,之于陈腐的“文以载道”(《文学小言》)、视悲剧价值远高于传统创作的“和谐团圆”(《红楼梦评论》),甚至大胆综评:“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均是惊世骇俗之论,世人为之瞩目。要之,王氏毋乃意在再造文明,而非汇通中西。即便他后来在《国学丛刊序》(1911)中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其底蕴着重在开展新时代的风气,以打破保守、怠变之习,而非意在调和新旧、中西之学。
另举“翻译”事例,以概其余。缘清末西洋文化长驱直入中国,新名词,包括洋译名和日译名蜂拥而至;哲学一门尤是如此。五花八门的新名词,令阅读群众目眩神迷,难以适应,因是卫道之志忧心忡忡,连一度是激进分子的刘师培(1884—1919)皆挂心新名词的输入,将导致民德堕落,遑论教育的当权者张之洞之辈。王国维则对“新名词”的涌入,保持开放欢迎的态度。他言道: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论新学语之输入》)
然而,他对国人译名颇有意见,例如:严复的中文译名若“天演”(evolution)、“善相感”(sympathy),则颇致微词。盖他认为日译名因群策群力,比起单打独斗的中译名更加精湛审慎,无妨多予接纳。王氏确言之有故,盖近代日本接受西洋人文学的知识比起中国更为积极,例如:史学方面,日方于1887年即延聘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关门弟子律斯(Ludw ig R iess,1861—1928)至本土,直接传授日尔曼史学近15年;哲学一门,洋人更是络绎于途,接踵而至。1887年康德学专家布塞(Ludw ig Busse,1862—1907),也亲自执教东京大学哲学科5年。因此容易形成群聚的加乘效果,以翻译事业而言,当时的中国只有瞠乎其后可言。

罗振玉◆“真正对(王国维)哲学的致命一击与意向的骤变,尚俟罗振玉的介入与劝导。”
原来辛亥革命(1911)之后,他随罗振玉再次避居东瀛,寄居京都,达5年之久。缘受罗氏大力规劝,转而改治经史之学,王氏遂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中《静安文集》百余册,悉加烧毁(罗振玉《海宁王忠慤公传》)。按《静安文集》乃是王氏亲手底定的文稿,收集了他近年研读西洋哲学的心得,并运用至中国学问的实验成果,再附上为数不多的诗作。然而一旦他幡然醒悟,竟至弃之如敝屣,改变不可谓不大,而将《文集》焚毁不啻宣示其破釜沉舟的决心。之后,王氏乃尽弃前学,为学判若两样。
惟个人揣测王国维在1911年再次东渡日本,固然经罗振玉的规劝,方才改弦更张,毅然步上研究国学一途。但在此之前,他恐尚未放弃追寻西方哲理的念头;否则他断不会不辞舟车劳顿,将那些攸关哲学的洋书,随身携至东瀛,并暂存放京都大学图书馆。然而一旦王氏旅日既久,以他的聪明才智和求知的热忱,不歇时便会知晓其时日本西方哲学研究的水平远非他所及[日本哲学界该时不止已迈入新康德主义的阶段了,而且进入西哲百家争鸣的状况。实言之,王国维个人所掌握的康德哲学相较于该时日本整体哲学界乃瞠乎其后的。参较牧野英二著,廖钦彬译《日本的康德研究史与今日的课题(1863—1945)》];而在知己知彼之后,果要在治学上出类拔萃,善尽己之长,“返归国学”不失为正确的抉择。
总之,王国维的哲学工作或许仅止于此一阶段,固然有其时代的意义,但真正影响及日后学术的发展,却是他接受西方史学以及接轨国际汉学的机缘。居中最关键的人物,不外是其业师藤田丰八和一路栽培他的罗振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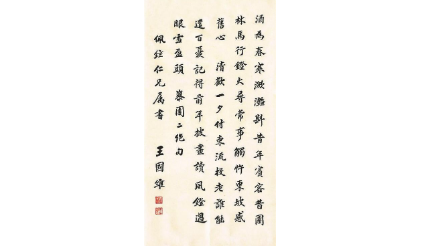
王国维书赠朱自清诗轴
王国维之接受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iography),盖经由藤田的熏陶。藤田毕业于东京大学,该时恰是兰克关门弟子律斯赴日执教的时候,藤田一辈的汉学家不少受教于他,而受到兰克史学的洗礼。这同时是近代日本史学转化的契机。尤其当时日本“东洋史”的研究倾向,乃是向西方请益,而非向中国学习。而王氏最初认识兰克史学,也是因为藤田嘱其代为写序之故[《东洋史要序》(1899)]。
简之,兰克史学对日本或中国“新史学”的启示,最重要的无非是重视“原始史料”与史料的“系统”性而已。这点在藤田或王国维的史学实践发挥得鞭辟入里。王氏就曾称誉备至藤田氏攸关中国古代棉花业的分析,其优点便是善用许多吾辈不能利用的材料,而引为己方憾事。要知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乃始自研究西洋哲学,因此纵使有接触兰克史学,但其影响一时并不显豁。惟一旦他跨入文史领域,其作用则立竿见影。例如:他在准备《宋元戏曲史》之前,则先大量广搜材料,编纂了《宋大曲考》《优语录》《戏曲考源》和《录曲余谈》(1909)等,这或可视为兰克史学典型的进路。
另方面,即便王氏为中国古史研究提出兼顾“纸上史料”与“地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究其实,考古学之所以引起他研究的重视,全因为文字材料发现丰富。这恰恰呼应了他一贯所主张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然而不容讳言的,王氏却依旧未得超越兰克拘泥于“文字材料”的专注,而达臻近代考古学的水平[这方面,犹俟之后的傅斯年(1896—1950)又往前推进一步,正视考古遗址于非文字方面的价值与重要性。请比较拙文《机构的宣言:重读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王国维步上国际汉学的另一引导者,正是罗振玉。其佐证之一,便是他少时素不喜《十三经注疏》,甫受新潮洗礼,即驰骋西学,游骑无归。此时却因罗氏规劝他“专研国学”,遂幡然一改旧习,尽弃所学;随罗氏请益小学训诂之事,并勤研《十三经注疏》,打下日后董理国学扎实的底子。这虽让他得以领会并承接有清一代的学术,却仍不足以尽道其日后绝大成就的底蕴;诚如他胞弟王国华(1886—1979)所言:“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又,王氏多年的挚友——金梁(1878—1962),且进一步称他“尤善以科学新法理董旧学,其术之精、识之锐,中外学者莫不称之”。
另有一项因缘亦不容忽视,便是罗氏和藤田毫不藏私地引荐了王氏与日本与国际汉学界直接切磋、交流(王氏即早便了解藤田在学术交流的关键性。他在1899年致汪康年的信,便指出“其所交游固皆彼中极有才学之士,若一旦不合……彼中材智皆将裹足不为国用,此事关系非小也”),让他接引上实时性的学术议题,一展长才。总之,毋论就原创性的见解或开拓崭新领域两方面,日后王氏均能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而为众望所归。末了,且援引王氏学侣——狩野直喜概括王氏一生为学特色的评论,以作为拙文的结语,他言道:
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卓越之处,一方面在于凡是中国老一辈大儒才能做到的事,他都做得到。……可是因为他曾研究过西方的学问,所以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为可靠。换言之,他对西方的科学研究法理解得极透彻,并将之用于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王君作为一个学者的卓越之处。[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按:狩野氏系日本汉学名家,但对本国和中国的古典研究均表不满,而有志于学习欧洲的研究法,早期问学甚受兰克史学的熏陶。在学术上与王国维时有往来。见江上波夫编著,林庆彰译《近代日本汉学家——东洋学的系谱》(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页71—78]
要之,狩野氏所谓“西方科学研究法”,意谓着无非是世纪之际,被奉为“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圭臬的兰克史学。职是,谓王氏甚受兰克史学的影响,虽不中亦不远矣!所以说,西方哲学对王氏的影响是一时的,而西方史学方是恒久的。
作者:黄进兴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李纯一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