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斯理安大学中国研究教授魏爱莲
魏爱莲成功地打破文学与历史的边界,在结语中,她将真实人物与小说人物并置,描绘了一幅闺秀演化图。如此一来,她也打通了明清文学与晚清文学研究:闺秀传统的转型与女权论述的兴起相联系,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与晚清新小说相对接,不变的则是詹氏家族对于女子才华的推崇,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切。
纵观晚清小说研究现状,学者的取径不外乎两种:一是现代文学研究者溯源而上,追索晚清小说的现代意义,譬如陈平原教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王德威教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2003),皆为此类研究的典范;一是明清小说研究者顺流而下,致力于探讨古典小说的新变,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2004)乃是个中翘楚。魏爱莲(Ellen Widmer)教授作为韩南教授的高足,其研究轨迹也发生了从明清到晚清的转移:早年完成的专著《乌托邦的边缘:〈水浒后传〉与明遗民文学》(The Margins of Utopia:Shui-hu hou-chu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ng Loyalism,1987)由陈忱的《水浒后传》切入,绾合了小说续书与明遗民研究;近年出版的著作《美人与书:十九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The 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06),关注的是清代闺秀与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因缘;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刊行的《小说家族:詹熙、詹垲与晚清女性问题》(Fiction’s Family:Zhan Xi,Zhan Kai,and the Business of Women in Late-Qing China)一书,则是她晚清小说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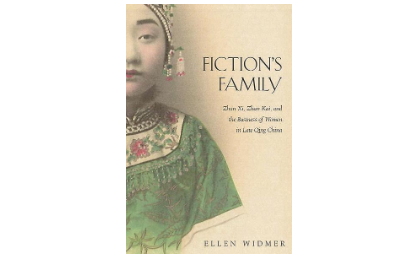
《小说家族:詹熙、詹垲与晚清女性问题》(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
相对而言,《小说家族》涉及的晚清新小说、女权论述、社会改良等议题更契合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旨趣。魏爱莲却另辟蹊径,将明清文学研究的思路纳入书中。她独具慧眼,以家族史为视域,研析浙江衢州詹氏家族的文学书写,跨越了王庆棣(1828—1902)、詹嗣曾(1832—1894)与詹熙(1850—1927)、詹 垲(1861?—1911?)两代人(也稍稍论及詹熙的儿女)。詹氏家族中,母亲王庆棣、父亲詹嗣曾活跃于道咸年间,魏爱莲将二人的经历与著述视作詹熙、詹垲两兄弟的创作背景,勾勒出从古典到现代的文学转型轨迹。在此基础上,魏爱莲突出詹家两代人对于女性问题的持续关注,揭示家族文学事业如何上承清代闺秀文学传统,下启晚清女权论述,将明清与晚清女性研究融为一炉。
不过,即使读者对学界潮流所知不多,仅从钩沉辑佚的角度考察《小说家族》,也足以增进对于晚清文学的了解。曾几何时,《小说家族》的研究对象湮没于厚重的历史尘埃中,我们跟随魏爱莲的笔触,有幸窥见詹氏族人的真容:母亲已非泛泛之辈,王庆棣与袁枚的女弟子酬唱往来,文名颇著;兄弟亦是一时俊彦,詹熙、詹垲熟识邹弢、吴趼人、李伯元等晚清知名文人,先后投身上海新闻出版业,其著作亦流行一时。由此可见,魏爱莲虽然以家族史为视野,但并未画地为牢,她藉由再现两代人的交游网络,彰显文学书写与时代的互动。
正是在前述思路下,《小说家族》娓娓述说詹家两代人的文学事业。除却绪论(第一章)与结论(第七章),全书主体包括五章。第二章关注王庆棣与詹嗣曾的生平与诗词创作。魏爱莲指出,王庆棣实为典型的江南才女,她年少成名,无论是《织云楼诗草》(1857),还是其唱和网络,在在显示她与闺秀传统的关联;詹嗣曾则是颇为常见的传统文人,早年困顿场屋,后为左宗棠门下幕僚,闲时吟诗作赋,留下《扫云仙馆诗钞》(1862)。两人文采风流,乍看仿佛明清女性研究者所谓“伙伴式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的典范(参见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魏爱莲细读他们的诗作,却发现这对夫妻绝非琴瑟和谐。——两人聚少离多,王庆棣独力支撑家庭,难以抑制怨怼之音。王庆棣似乎将自己的抱负寄托于文学创作中:她在丈夫的支持下,公开刊刻个人诗集;她又借助儿子詹熙的交游网络,将诗作发表于上海申报馆的文学期刊《四溟琐记》(1875)之上,从而涉足商业出版。凡此种种,皆开风气之先,显示詹氏家族重视女子才华,亦反映闺秀传统遭遇变革。
第三至六章转向詹氏兄弟。魏爱莲先探析哥哥詹熙的生平及著作,尤其是白话章回小说《花柳深情传》(1897)。经由韩南教授的研究,学界对这部作品已耳熟能详(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1895年,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发起征文,号召创作小说以批判“三弊”——缠足、鸦片、时文,进而改造中国社会。詹熙的小说并非参赛作品,但明显是对征文的回应,可谓新小说的先声。小说主体围绕衢州魏氏家族在太平天国前后的遭遇展开,描述沉溺于“三弊”的魏家兄弟如何幡然醒悟,期待警醒读书人。魏爱莲勾稽出詹熙的经历,作为解读小说的前提:早年于上海卖文为生,甲午之后忧心家国命运,从事小说创作,随后返乡投身女子教育事业,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士绅。魏爱莲随后细绎文本,发现詹熙在创作小说时既依据了詹氏家族的历史记忆,也注入了自身的改良愿景。就前者而言,小说中詹家在太平天国时期的逃难经历,与詹嗣曾、王庆棣夫妇的相关诗作相对应。就后者而言,詹熙着力塑造了理想的女性形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家女仆雪花:她保留天足,年富力强,于战乱中救护魏家女儿阿莲,又于战后主持家务,重振家声;在她影响下,魏家女性纷纷放足,雪花也成为魏家二公子侍妾。在现实中,詹熙与他的子女詹麟来(1877—1919)、詹雁来(1891—?)于数年后在衢州倡导天足,推动女权,兴办女学,竟然将小说转化为现实。颇具意味的是,维新志士詹熙寻得了改造社会的良方之后,也就全然放弃了小说创作。
全书的重头戏是关于弟弟詹垲的研究。魏爱莲以三章篇幅分别讨论其生平与花谱创作、小说创作,以及报章文字。与兄长詹熙不同,詹垲完全融入了洋场文人的世界。他大概于甲午战后离开家乡,长年寓居海上,既流连于青楼妓馆,又担任报章主笔激扬文字,最后客死异乡。最能展示詹垲“风流才子”形象的作品,莫过于《柔乡韵史》(1898)、《花史》(1907)、《花史续编》(1907)等花谱。魏爱莲认为詹垲继承了《板桥杂记》等狭邪笔记的书写传统,又引入时代思潮。较早问世的《柔乡韵史》依然不脱访艳指南的套路,为文人寻花问柳提供津梁。随后的《花史》正续编则翻转此一传统,面向女性读者写作,沾染了启蒙色彩:这些风尘女子小传的传主不仅文采斐然,而且富有公德心与爱国心;她们创办学校,赈济灾民,反对西人侵占路权,简直令传统闺秀相形见绌。与之相应,三部作品背后的书写者形象也发生衍变,从品鉴青楼女子的浪荡文人转化为忧国忧民的志士。詹垲此时正在编写《全球进化史列传》(1903)等世界伟人传记,这也证明他在声色犬马之外,从未放弃对维新事业的追求。

詹垲的两部改良主义小说《中国新女豪》与《女子权》,均浙江图书馆藏
与此同时,詹垲借助两部改良主义小说《中国新女豪》(1907)与《女子权》(1907),宣示了他的“新小说家”身份。詹垲的小说创作比兄长晚了十余年,虽然同样旨在改造社会,但叙事架构已不同于《花柳深情传》,针对的读者也不再是男性文人。这两部小说情节类似,讲述英娘/贞娘接受女子教育,萌生女权思想,投身男女平权事业。两位闺秀或是创办报章,或
是建立妇女自治会,又游历各国,提倡女子职业教育,最终蒙皇帝赞许。魏爱莲凭借对于晚清小说的熟稔,追溯两书的影响来源:《雪中梅》之类明治日本政治小说为詹垲提供了“未来记”的情节模式;王妙如《女狱花》(1904)、海天独啸子《女娲石》(1904)、汤宝荣《黄绣球》(1905—1907)等女权小说论及的女子选举权、婚姻自主、职业自由等议题,亦在詹垲笔下引发的回响。作为对照,本章还讨论了詹垲的文言小说《碧海珠》(1907)。在此艳情小说中,作者返回书写花谱的传统,在描摹理想闺秀之余,詹垲保持了对烟花女子命运的关注。

《女狱花》(1904)和扉页上的作者王妙如像
詹垲的报人经历,对于他的文学事业也至关紧要。詹垲辗转于上海、北京、汉口,先后担任《商务报》、《汉口中西报》主笔,撰文提倡商务、宣传立宪。在创作小说时,詹垲关于立宪、立法的观点,亦在故事情节中展露无遗。有趣的是,魏爱莲指出,《中国新女豪》与《女子权》两部小说开篇等处的议论文字,其实运用了政论的笔法。不仅如此,小说女主人公英娘/贞娘亦阅读报章、创办报章,政治关怀深深切入了詹垲的小说创作。魏爱莲认为,在詹垲涉足的诸多文类中,政论与小说最为贴近,原因在两者皆旨在说服读者,只不过前者面向男性,后者针对女子。
在阅读《小说家族》的过程中,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魏爱莲对于一手文献的孜孜以求。詹家两代人文名不彰,著作散落于衢州、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图书馆中。魏爱莲“上穷碧落下黄泉”,走访各地收集研究资料,广泛参考地方志、诗文集、报刊,最大程度地复原詹氏家族历史,展现了史学家的深厚功力。与此同时,书中的文本分析亦体现了文学研究者的本色当行。书名为《小说家族》,小说是核心文本,但魏爱莲不以文类为限,而是涉及诗词、花谱、报章文字等各类作品。她尤其善于对读不同文类的文本,或是将小说可能的影响来源一一掘发,在对比之后彰显出詹熙、詹垲的继承与创造,或是考察不同文类如何呈现同一议题,又如何对应不同性别、阶层的读者,在展示兄弟二人思想延续性的同时,彰显出不同文类的规范。
在此基础上,魏爱莲成功地打破文学与历史的边界。譬如在结语中,她重新梳理线索,将真实人物与小说人物并置,描绘了一幅闺秀演化图:从王庆棣、魏阿莲、詹艳来到英娘/贞娘,从缠足到天足,从偏居一隅到出访海外,从涵泳诗词到阅读教科书、创办报章……她们逐渐走出闺门,拥抱现代。如此一来,魏爱莲也打通了明清文学与晚清文学研究:闺秀传统的转型与女权论述的兴起相联系,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与晚清新小说相对接,不变的则是詹氏家族对于女子才华的推崇,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切。正是在此意义上,《小说家族》足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带来启示。
虽然全书创获颇丰,但是囿于资料的限制,魏爱莲在书中提出的部分关键问题未能得到完满的解答:譬如王庆棣对于女子地位的看法,以及作为女子的艰难苦痛,是否直接促成了詹熙、詹垲两兄弟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兄弟二人的著述屡屡涉及职业教育、女性问题,两人的观点如何交互影响?令人颇感遗憾的是,王庆棣、詹嗣曾现存的诗词对于家庭生活的记录只有三言两语,詹熙的《绿意轩诗存》与詹垲的《幸楼诗文集》皆已失传,研究者难以再现詹家两代人的生活轨迹、家庭教育的细节以及兄弟交往的详情。因此,《小说家族》引入晚清小说家汤宝荣,借助间接证据做出推论。汤宝荣为詹熙、詹垲好友,又与两人的小说创作交互影响:汤宝荣妻子放足的经历可能为《花柳深情传》提供了相关素材,詹熙创办教育事业的艰辛历程则进入《黄绣球》文本,《黄绣球》对女子教育的重视与男女平权思想又影响到詹垲的小说。除此之外,汤宝荣的闺秀母亲课子的记录亦为魏爱莲提供凭据,藉以推测王庆棣的教育方式。当然,若要严密论证前述问题,我们只能期待更多新材料问世,为《小说家族》补足关键的证据链。
事实上,魏爱莲的上下求索已经触发了新资料浮出水面。2015年9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刊行了《衢州文献集成》,包含二百三十八种著述,詹家两代人的作品皆在其列。笔者注意到,《衢州文献集成》纳入的詹熙编选《兴朝应试必读书》,魏爱莲尚未及寓目。此书刊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时值百日维新,推行科举新制,废去八股,改试策论,詹熙积极响应朝廷新政,推出此科举用书,包含《史论》《时务论》《国朝政治策》等门类。詹熙在序言中痛斥八股取士之流毒,正堪与《花柳深情传》相对照。他在书中大量选入《西人所著公法可恃而不可恃论》等自著文章,可见其自我期许与用世之心。除此之外,书中还搜罗了弟弟詹垲、友人邹弢的不少篇目,若是仔细研读,我们对于兄弟二人的家国情怀、知识结构以及思想交流也许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由此看来,晚清文学资料与历史文献的大量重印为我们重探晚清文学提供了绝佳时机。顺着魏爱莲的研究思路,我们不妨继续追问:晚清中国是否还存在类似的小说家族?他们在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境遇如何?在江南闺秀与文人传统之外,其他地域的小说家族如何因时而变?又如何万变不离其宗?《小说家族》足以提醒我们,只有引入明清文学研究的视野,才能够更深入地考察晚清文学变革。毕竟,虽然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一代人思想的底色依然是传统。
作者:崔文东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研究助理教授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李纯一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