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周作人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平民文学》一文(《每周评论》第5号),明确提出新文学必须坚决反对贵族文学,代之以记叙普遍和真挚思想感情的文字。此前,陈独秀已经喊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的响亮口号(《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此文可以说是对这一口号的详细阐述,从此平民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一大标签。
从出身来说,周作人不是平民,发表《平民文学》时的身份是北大文科教授;陈独秀是他的顶头上司——北大文科学长。他们身边的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学同仁,没有一个是白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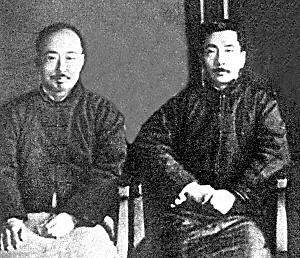
周氏昆仲
由鸿儒们建设起来的平民文学必然带上精英的色彩。思想上的反礼教和西化不用说了,就是语言,虽然经胡适首倡,用白话取代了文言,但也并非老百姓的口头语,而是一种相当欧化的汉语,最显著的表现是西式的语法结构和标点符号,以及新的词汇。这样的文学显然不接地气,普通老百姓——平民——很难一下子就接受,更谈不上喜欢了。实际上,直到1924年,茅盾依然坦陈“新文学尚没有广大的读者界”,因为“要养成一般群众的正则的欣赏力,本来不是一朝一夕所可成功”(《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鲁迅的母亲,她从来没有读过《呐喊》《彷徨》,只喜欢张恨水的小说。
五四新作家不仅反对古代文学,也反对以张恨水为代表的当代通俗文学,他们对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不仅因为双方的文学主张完全不同,也因为后者占据着巨大的读者市场。五四文学虽然是新潮,但读者只局限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此周作人早有预见,他在《平民文学》中明确地指出:“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勇于担当“先知”和“引路人”,无疑值得钦佩,但和平民之间的距离感也十分明显。
沿着这个思路再来看鲁迅关于“铁屋子”的那段名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呐喊·自序》)不管鲁迅的基调多么绝望,他分明还是把自己放在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和“少数者”之列,和乃弟周作人的自我定位完全一样。
1932年瞿秋白反思五四新文学时尖锐地指出,“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以及纯粹从这种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初期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他甚至认为这种文学对于民众是“白费”。瞿秋白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立论的,话讲得可能有些过头,但他指出的问题并非毫无针对性。五四文学运动以平民的名义发动,但又以批判平民,至少是教育和引导平民为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内在的矛盾。
(节选自顾钧《文学史上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全文见2019年5月15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顾钧
编辑:任思蕴
责任编辑:任思蕴
来源:文汇学人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