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上海人解析》《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海派映照下的江南人物》三本书中探讨的问题归集到一点,就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城市的集聚功能。这个问题如果细分开来,可以分为三个问题:人口集聚、人才集聚和文化集聚。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努力探索的一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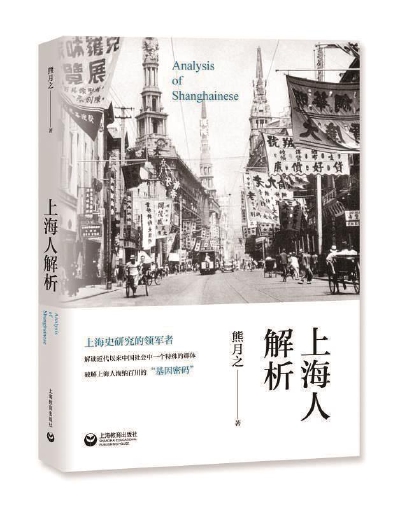
从城市的集聚功能看近代上海发展的“创新基因”
众所周知,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前人口才20来万,有一种说法才12万,到1949年已经达到546万,那么多人口主要是外来移民,非上海籍占了85%。城市史研究的结果说明,城市人口大规模的集聚一定会带来两个极为明显的效果:一个是创新力增强;一个是人均资源消耗率降低,即人均碳排放降低。这当中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因为城市道路、交通、住房、绿地由于规模效应人均占有率一定是远远低于乡村和小城镇。
就创新能力增强而言,其学理也比较容易说清:城市人口规模越大,人们互动交流的机会就越多,创造与创新的能力也越强,人口集聚必然带来行业竞争,行业竞争必然会导致分工细化,分工细化必然会刺激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必然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结果势必增强城市对于人口的吸引力,从而推动城市跃上新一轮集聚、竞争、分工、创新、进步的循环。
近代上海在创新方面可以举出很多生动的例子。比如商务印书馆之所以长期执中国出版界的牛耳,就是因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出版内容,印刷设备持续翻新,管理制度不断革新。企业繁荣发达的关键也在于创新,荣德生先生曾经将企业发达的秘诀归结于设备力求更新,一些从事生产替代进口产品的民族企业持续不断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以改进落后生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关曾经对上海270家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工厂都拥有从国外进口的先进机器。上海有名的“棉纺大王”穆藕初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棉纺业巨头,关键就是在于他看重机器和管理的创新,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作为近代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之一,陈光甫的成功之道也在于创新。他在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开始只有区区七八万元的资本,7个员工,但特别注意吸收不为其他大银行所重视的小额存款,1935年发展到40多家分支行,资本达到500万。
创新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汰。1912年到1927年上海新开的企业至少有1194家,但是到了1927年年底实际上还在开工的只有795家,仅仅占15年当中新开工工厂数量的66.6%。换句话说,新开业的工厂至少有三分之一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停工歇业了。优胜劣汰,从被淘汰企业角度来讲是非常残酷的,但是从整个城市创新能力提升角度来看又实属必然。
近代上海在文艺方面包括绘画、戏曲、音乐等等,饮食方面,服饰方面都是如此,诸如任伯年这些画家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海派京剧之所以风靡全国,越剧之所以在上海唱红,上海电影之所以能够展映整个中国等等,固然少不了市场定位准确、品质优越、服务周到等因素,关键还在于创新。

任伯年作《荷塘鸳鸯图》
上海为文化交融文明互鉴提供了先驱性的经验
人口集聚有利于人才成长。近代上海,很多外来移民一开始都是很普通的民众、很普通的学者,后来在城市当中锻炼成长,有的成为杰出人才。我曾经研究过106个从普通学徒成长起来的各类著名人物的历史。像陈云,如果不是到上海,他的人生轨迹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像王开照相馆的王炽开等等,原来都是学徒,后来成为了上海的成功人士。
城市的集聚功能还体现为人才集聚。除了普通人在城市里成长为杰出人才,还有一种情况是,人才受到上海城市的吸引而来,于是有了更好的发展舞台、更高的起点,来到上海后有了更优秀的发展,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如果我们注意研究上海人才史的话,比如鲁迅、巴金,他们来上海以前事业上已经开始成功了,到上海后就更为成功。这是上海城市的吸引力将他们拉来了,他们来了以后,又增强了城市对于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第三是文化集聚。不同地方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上海集聚,刺激了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和借鉴。近代上海租界虽然其中98%的居民是中国人,但是无论市政规划、城市风貌、市政管理,还是管理背后的市政理念都是从欧美搬来的,与上海大异其趣。相当一部分西方人把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他们将欧美的国际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搬到上海。租界里体现各种西方科学技术的机器设备,包括宽阔马路、明亮的橱窗等等,都是西方科学技术的载体;租界里各种各样的制度,比如纳税人会议制、司法制度、选举制度、招商管理制度等等,都是从西方搬来的。西方人种种的行为方式都成了体现西方人精神风貌的一种表现。租界变成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化、租界和华界明显的差距,极大地刺激着上海人,推动着上海人学习西方的步伐,像煤气、电灯、自来水的使用,篮球、足球、赛马等运动的开展,都是西方人开展在前面,中国人仿照在后面。
近代上海有一点点像“小联合国”,世界上五六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在这里生活工作,不少人以此为家,他们自称是上海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世界各地的文化,各种文明带到这里,使得不同文化和文明在这里得以自然地相遇交会,互相借鉴。
比如,人们很早发现上海有那么多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除了中国本土的道教,早已中国化了的佛教,其他的像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等上海人都很熟悉,在上海无一不有,但是上海没有发生过什么激烈的教案,没有什么骇人听闻的宗教冲突。这个问题晚清时期西方人就很奇怪,说中国内地天津、河北、山西都有那么多教案,上海为什么没有?不光没有教案,而且从20世纪初开始,有一批又一批中外有识人士在上海讨论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如何互相取长补短,和谐相处,这个讨论持续了至少15年,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的很多著名学者都参加到这个讨论当中,当然也有数量可观的中国学者参与其中。我们今天回过来看,他们的讨论比美国学者提出的文化冲突问题要早了将近一个世纪。
今天,不同文明之间如何避免文化冲突这一问题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上海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先驱性的地方性经验,这一点也是上海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作者:熊月之
编辑:刘力源
责任编辑:杨逸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