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儿子大野健介告诉父亲自己打算辞职的时候,作为父亲的大野武史沉默了。话到嘴边,却只剩下了一声叹息。
可他内心却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健介的老家在三重县,高中毕业之后,他升入国际基督教大学(ICU)教养学院的理学科开始了大学阶段的学习。在这之后,他又获得了北陆尖端科技大学院大学的硕士学位。在大学研究室的推荐之下,他进了一家鼎鼎有名的大型电机公司工作。
作为父亲,面对儿子这种无可挑剔的履历,他心里无疑是暗自感到骄傲的,当然,也一定是十分欣慰和满意的。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半时间,儿子健介便提出要辞职换工作了。
这不是商量,而是一声通知。早在告诉他这个消息之前,健介就已经看准了另外一家大型电机公司,将之作为自己的跳槽目标企业了。当时,健介仿佛毫不在意似的,轻描淡写地对父亲说了一句:“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辞职想去那家公司。”
没有怨言是不可能的。再怎么说,健介原先所在的公司也是总体员工规模达到10万人、日本巨头企业的代表之一。他想,好不容易进了公司的研究所,就不能继续待上几年以后再做选择吗?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二十七岁已经有了自身判断能力的儿子,他不知道自己的话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四年后(2008年)就要退休的大野现在已经五十六岁了。他在四十岁时离开了位于关西的石油化学公司,跳槽来到了现在的公司。从那以后,他便经历了很长一段离开家人前往公司“单身赴任”的时期。所以,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父亲。正是因为联想到了自身的职业经历,他才没对儿子的跳槽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而且,他回想到在自己将近三十五年的职业生涯中,本身就与职场上跳槽辞职的年轻人有过很多接触。
最近有时论批评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刚入职就辞职的案例近年来比比皆是。但他觉得,年轻下属的跳槽无论放在今天还是放回以前,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很早以前,在他自己的下属当中,这种入职即辞、速度之快令人咂舌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不仅如此,主动要求公司内职位调动的人,也不在少数。
“跟想象中有很大差距。”年轻下属们几乎都是同样的说辞。也就是说,儿子健介并不是一个特例。
他又想到,其实这也可以理解……
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对于父母所说的话,不也是不闻不听更不愿意照做吗?
“我出生的年份是1947年,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正好是团块世代的排头兵。”
为了对健介的情况进行了解,我首先拜访了他的父亲大野武史,一开头他这样对我开口说道。
他永远也忘不了刚进小学时老师对他们讲的话——“孩子们,要知道你们是日本人口数量最最庞大的一代哦,所以今后无论在哪个领域里,你们与同伴之间的竞争都是很激烈的。”
健介的父亲深有感触地说:“老师讲的话果然没错。”在学校,一个班通常有60个孩子,之后无论是升大学还是在企业里面工作,同一代人之间的竞争感觉上都是异常激烈的。
大野继续讲道:“当时,工作在我脑海中的概念就是在战后复兴的最后冲刺阶段和形势逐年向好的时代中像熊熊燃烧的炭火一样毫无保留地尽自己的那份力。那是一种在转动的齿轮上不断向前奔爬的感觉,只不过这种齿轮比你们想象中转得更快,不拼命保持高速运转的话就很有可能因为跟不上节奏而掉队。我们公司生产的是多孔塑料,因为是非垄断性质的生产经营,所以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生产效率在行业内脱颖而出,就成了公司的首要课题。这样一来,我们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就需要不断追求更高水平的合作性与协调性。其实从这里就可以发现,不是因为日本人自身努力工作才使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而是因为本身处于那样的时代,我们工作起来才那么拼命。”
但是,要让健介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对上述时代有所体会则是不现实的。健介自己也说过:“辞职的理由太过琐碎了,连我自己都不一定理得清楚,更别说跟他们解释了。”也许这就是他只把自己的最终决定告知给父母的原因。在这一点上,父子俩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横亘在他们中间的时代“鸿沟”。
“现在确实是不同了啊,健介他们这个时代!”大野武史感叹道。
他继续向下说:“这个时代的齿轮转得慢多了。如今,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上虽然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整体来说,获取个人成功的通道却变窄了;而以前,就算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小,但个人却更加容易取得成功,两个时代的差别就在这里。而这种差异正好通过两代人的工作观念与意识表现了出来。如果齿轮本身转得很慢,自己又在精神上有所松弛的话,保不准就会从齿轮上滴溜溜地掉下来。为了不致堕落,必须找到相应的着力点,自己让齿轮快速转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代身上背负的压力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大。”
“但是……”他中间停顿了一下,就像要事先告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一样,又开口说道:
“齿轮虽然会因为跟不上周围的节奏而掉队,但与之相反,如果单个个体速率过快,整体也同样不能正常运转,所以既要保持高速运转又要与周围做好协调与配合。我们当时那一代人,就处于这样一种左右都有顾虑的状态。”
他们那一代年轻人所特有的“不安”与健介他们所感到的“不安”,也许是有着本质差别的。但是,这种不安却并不应该由“时代”来买单。不同时代的不安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对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个体来说,大环境却都是相同的。
“你自己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对着看起来尚缺稳重的健介,大野武史曾这样说道。

就像老话经常讲的那样,只要是做一项工作或者长时间担任某种任务,到了一个月、三个月、一年或三年、五年甚或更多时间节点的时候,不知何种原因,人就会在工作心态上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具有周期性的。在这些时候,自己怎么调节心态,以何种方式解决问题,对成人来说这是他们的自由,但对社会人来说则是他们身上需要担负起来的责任。两年半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现在早就与过去的时代不同了,父母再想指挥子女这样那样已经不现实了……
健介想起从前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大学毕业之前我们还可以给你负担各种费用。但是至于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工作,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为你自己负责。”
“以后,如果万一到了想换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考虑过后再做决定,不要到时候接二连三地换了一次又一次。千万不要抱着‘别人碗里的饭菜更香’这种心态轻易去换工作……”
这是在心里隐藏了许多话的大野武史对儿子提出的唯一建议。
被城市郊外的绿植所包围起来的研究所到了人声逐渐湮没的夜晚时分,就融入一片带有薄薄一层湿气的静谧当中去了。
偌大的房间里整齐地排列着大约15套桌椅,要不是地板上加铺了一层地毯,这里就完全是一间教室的感觉了。在这个空间里,则根本听不到任何一句多余的话,周围都安静得快要让人窒息了。就算已经到了午夜12点,还有好几名员工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电脑液晶屏,与之相伴的,是起起落落的键盘敲击声、密集的鼠标点击声、文件翻页时纸张的摩擦声以及空调低沉的呜咽声。
与总部办公楼里那帮人天天西装革履的打扮不同,研究员们大都穿着比较随意。
隐藏在办公室的一角,坐姿一直较为随性的大野健介暂时停下了敲击键盘的双手,他对显示在电脑液晶屏上的文章和公式反复确认后,终于打开了文件菜单选项,选择“打印”点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便传来了办公室总打印机自动运转的声响。
他站起身来把刚打印好的稿子在手里整理了一遍之后,就拿着它们去向科长交差了。他们科长大概在三十五岁左右,好像知道他要过来交稿似的,顺势便接过他手里的报告将之叠放在办公桌上了。
这就是在这两年间重复了无数次的操作。
科长做完自己手头的工作之后,应该就会着手审查他的稿件了。
健介想道:“可就算这样……”
“究竟这回又要重复修改多少次呢……”
对于论文质量的好坏,他逐渐丧失了自我评判的能力。每次交给上司检查,总是被打回来重新修改,到了再次提交的时候,又会收到新的修改意见。本来把论文交给科长以前,就已经让一位前辈反复帮自己看过了。接下来,好不容易通过了科长这一关,却仍然可能再次被部长推翻重写。那也意味着,又将重新回到原点……
这样的修改经历了一遍又一遍,他终于变得疲惫不堪了,各种条条框框让他丧失了思考的活力。想不出新的东西,推翻重写的部分仍是按照旧稿的文脉在走。渐渐地,仅存的那一点自信也从他体内一点一点地流光了。
实际上,他也对自己的上司隐晦地表达过,就算这样改下去最终跟他的原稿也并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但上司却将其作为一种年轻职员的“通过仪式”,继续进行着推敲。如果是展讲资料的话,大到文章内容结构,小到文章字符的统一,都要一一进行细致的确认。向客户展示的资料暂且不说,交给公司部长或者研究所所长的报告要求则更为严苛,这令他十分抵触。
“无论如何你也要继续改下去。”这是上司对他最后的嘱咐。
2003年春末夏初的时候,他已经在公司待了两年多,马上要迎来第三个年头了。
他们研究所包括通信、生命科学、数据库等几大主要部门,每个部门之下又分设了众多具体职能部门。他所在的部门专门负责超级计算机的开发与研究。每天,十几名员工同处一室,日夜钻研着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新。
这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健介颇受震动。一位入职快满两年的研究员向所长提交了一篇简短的小论文。文章主题在于两点,一是公司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超级计算机的研究究竟作何用处;二是这种研究究竟能对社会、对技术本身的提升有多大帮助。
在超级计算机的开发与研究上,他们的行业竞争对手是A公司。因此,他们绞尽脑汁所要撰写的文章就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那便是要挖出足够多的证据证明自家公司的产品在性能上比A社更为优良。在对计算机性能的评估上,有理论性能与实际性能这两大指标。前者大多跟物理性的条件相关,在整个行业公布的产品信息里早已有相关说明。
然而,产品的实际性能却要经过实际的编程运算才能够检测得出。当然,实际性能与理论性能越为接近则说明效率越高。
他写稿之所以如此绞尽脑汁,便是因为从实际性能来看,自家公司的产品确实比不上竞争对手。不用说基准判断指标,从单位面积性能、耗电量等多种角度上来判断,都是竞争对手更胜一筹。
如果在研究生院,接下来就可以直接按照实际测试结果撰写报告了。可惜在这里,所讲求的并不是纯粹的技术论,而是对于自家公司的偏袒和维护。虽然他被反复的改稿和文字游戏折磨得几近人格分裂,但却也不得不接受这就是自身工作的现实。
而他——或者说他们整个部门——所要做的便是找出自身的计算机产品在运算方式上所具备的优势。
A公司的产品确实在特定科学技术类的计算上表现突出,但他们公司的产品也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虽然在对实际性能的评测上A公司产品的优势可能更加明显,但在对各个领域数据的计算上,他们公司的产品则更具有“通用性”。
既然如此,便可尝试对这一项优点进行重点宣传。通过反复强调本公司产品在特定领域内的高效计算性能,“制造”出其在同类产品中的优势也不是不可能的。之后再运用分析所得结论,对超级计算机技术开发的意义与功用进行最大限度的宣传与渲染。
写作宗旨如此,内容上也自然格外重视“读者视角”了。上司之所以对文稿要求这么苛刻,也是想通过不断的修改让文章内容显得更具煽动性。在这里,文章论据和论证的科学性倒被放在了其次。
回到自己座位上之后,健介开始了静静的等待。过了一会儿,他用余光瞥见上司手里拿起了自己那一叠十页左右的稿件。
他手头已经没有其他任务了,只待上司将他的文稿看完。跟往常一样,他暂时把自己的情绪收敛起来,走向其他楼层的休息室。喝了一杯咖啡之后,他走进吸烟室,点燃了一支烟。在这个小屋里,只有排风扇不停运转发出的轻微轰鸣声。和着刚刚憋住的那一声叹息,从他口鼻中吐出了长长的一串烟圈。
一名年轻工程师的背后,却是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的凄凉与空虚。

入职以来,不仅在这一件事上,整个部门给他的感受都是相似的,“编造”、玩文字游戏的地方屡见不鲜。产品的实际性能问题,只不过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而已。
他戏称自己为“高级派遣员工”,那是因为,他们还要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对实际做开发和设计工作的事业部时不时抛出的突发性提问做出相应的回答。研究所的先行研究经费虽来自公司整体的预算拨款,但另一方面,负责产品制作生产的事业部也会向他们提供经费上的支持。他所在的部门多数业务的开展还得仰仗后者。
他继续向我解释道:“就超级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来说,并不是我们自行开发的,而是从其他公司购进的。就算应事业部的要求,需要测试出计算机系统的实际性能,但由于很多数据都拿不到手的缘故,在评测方面本身就存在一定局限性。而且其他公司对于我们这边的数据咨询请求也不可能全盘给予明确的回复。所以,我在撰写报告的时候,只能如实写上‘资料论据不足’,写出来的报告,我自己可是要负全责的。虽然有说法称这只是一种对既存产品的‘微调’,但对于写报告的人来说,实在是苦不堪言。”
他还有几个跟他同期入职的好友在其他部门,一问大家,基本上都有同样的感受。但因为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所以本质上仍旧是孤身一人。与他年龄差距最小的前辈也比他多了5年的工作经验,除此之外,便再没有跟他同一年龄段的同事了。他有满肚子烦恼想要倾吐,但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这样跟说谎造假又有什么区别呢?”好不容易能喘口气,他吸着烟将自己的大脑放空了,但这会儿他又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啊,不对!他并不曾在报告中说过谎,他的文章内容全都是有现实依据的。在某些领域的计算上,他们的产品确实比A公司更有优势;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测算出来的数值也的确有所上升。但是——
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报告里通篇都是对产品优点的片面宣传。
只能说这里面没有虚假的信息,但这跟实实在在的“事实真相”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当然企业也有企业自己的一套操作方式,从各种角度最大限度地宣扬本公司产品的特性和优点这种做法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
而且自己在报告中所分析的“在某种条件下”的优良性能在适用范围上确实也较为广泛。如今他们的产品在多种数据解析、科学技术计算等方面同样表现不俗,在激烈的竞争中尚可占据一席之地。并且,行业内其他竞争者同样会利用产品细节上的微小差异来做文章,并将其作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武器。在日本的这种行业现状中,自己这样的存在且不论好坏,对于公司自身的利益来说首先是必要的。从整体构造来看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
但即便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他还是觉得自己作为研究人员的骄傲与尊严被现实撕裂了。对此,他久久不能释怀。“服从企业的规则、唯企业所命行事”与“遵循自身价值观、在自我肯定中工作”之间,必定是有本质区别的。
如果回到企业内部视角,往深一步对“企业本身的正义”这种说法进行仔细推敲的话,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部门有部门独立的“研究正义”,提供研究经费的事业部有其“话语权正义”。再者,在这些之上还有覆盖全局的“整体正义”。
大野略显无奈地说道:“尽管要以‘研究关乎公司名誉’的心态尽量往好里写,但心里却明白这不过是公司为了存续所采取的手段。与单个部门不同,公司整体‘正义’当中也包含了对其经营的事业进行适时调整与修饰的内容。无论是主观感受上还是在技术层面,要是这种‘事业’已经丧失了竞争优势、赚不到钱的话,当然是趁早舍弃掉最好。可是,为了企业‘短浅的利益’,我却还要在论文中对实际上会对公司利益产生损害的‘事业’大肆进行宣扬。总体来说,就是要在多重‘正义’当中去找一个尺度,这个尺度跟最小公倍数或者最大公约数的性质差不多。”
无论如何,这份工作总让他觉得自己就是在“说谎”,然而他还得为自己亲手所写的报告负责。报告末尾虽然也明明白白地署有共著领导的姓名,但本公司所产超级计算机的“性能优点”却直接因为他的论证而得到了“强化”。
但这种吹捧却不是发自他内心的,他相信自己的上司也一样。
问题不仅仅在于与A公司的竞争。在他看来,就自己公司所生产的超级计算机本身来说,其价值也在不断贬值。
“要是在1995年以前——”他试着想象道。
那时这个部门里一定充满了活力。
流体力学、医疗、宇宙工学……所有科学领域中都导入了超级计算机系统,其强大的计算能力成功解开了许多困扰人类的世界之谜,诞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成果。而从事超级计算机开发的研究人员,必定对行业未来的发展抱有强烈的信心。毕竟,其研究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是作为研究者所能体会到的极大的乐趣。当然,如果背后没有大企业作为支撑,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搭乘着企业这艘大型飞船遨游在由梦想与传奇构筑的外太空中。这时个人与企业的关系,是令人幸福的互惠互利的关系。
但现在呢?
企业的态度是冰冷的,对于年轻的技术研究员来说,这里也并无梦想或传奇可言。大野之所以感到痛苦,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找不到可以下定决心攀附的“齿轮”。
经济泡沫虽然破灭,但新技术的发展却未止步。他之所以把自己称作“高级派遣员工”,是因为他所做的工作已经脱离了核心技术的开发,工作地点就算不在公司,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如今消费者所使用的电脑在性能上也取得了飞跃性的提升,如果不考虑外观,把这些市面上的电脑以一定数量连接起来之后,其性能说不定也能赶上现有的超级计算机吧。再看看在世界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与当时相比日系企业的比例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超级计算机研发本身是必要的,但他在自己这个部门当中却感受不到这种研发的“必要性”。尽管如此,公司却还想保持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那场华丽的“传奇”。
提到大野的遭遇,当时经常跟大野一起喝酒的一位公司同期员工似乎也深有感触,他开口说道:
“就算在同一个公司,各个部门的情况也不一样。不过,他们计算机硬件组是最让人感到窒息的一个部门了。在世界市场竞争中也惨遭挤压,国内国外的市场占有率都少得可怜。明明跟竞争对手相比已经落败了,却还不让人讲出真相,所以就只能在说辞上做文章了。拼命地强调着在‘哪些方面第一’、‘哪些领域有优势’,明明很差劲的东西还要一个劲儿地夸赞,当然会让人觉得心里难受啊。
“遗憾的是,还会有很多客户非常重视这种‘某些方面的第一’,做这些客户的生意对公司来说仍然可以盈利,但这改变不了产品性能落后的本质。到头来,这让公司里那群老人抓到了继续鼓吹产品优势的理由,并且丝毫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大野对自己的工作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工作上的热情。以大野为首,就算整个部门都认为这种“性能优势”几乎不值一提,但违心提交上去的报告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公司的“官方评测结果”。想到这种报告正在一页一页地堆积起来,大野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窒息感——
至少有一个也行,在这个部门继续待下去的理由。比如,一个通往成功体验的目标。
大野继续讲起了他的团队观,说道:“上面的领导说不定还觉得我们这些家伙不够圆滑、假清高,但实际上我们比谁都想要结成一个和谐互助的团队。说真的,聚会上的那种连带感有没有其实都无所谓,我想要的是工作上的那种连带感。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怎么怎么样的,就像电视剧里面的那种情节。”
上司正是曾经在这个部门中有过“成功体验”的优秀工程师。大野回到办公室,上司正认认真真地阅读着大野所撰写的报告,尽管这份报告在大野自己看来百无一用。
他继续述说着自己的感受:“觉得这个工作没什么意义之后就只剩下厌恶的感觉了。直接给客户阅读的报告反倒比较少,整天就是为所长或者事业部写报告、写说明材料。说它无聊可能会显得我比较狂妄,但这种工作做起来确实价值感很低。”
就像他父亲在无意识中所提到的那样,“如果自己在精神上有所松弛的话,就会从齿轮上滴溜溜地掉下来”。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明显地感知到了这种“堕落”的不安。
话快到嘴边了,以前他绝对不会说出口的那种抱怨——
“这跟我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想成为一名技术工程师的理由之一——能为科技、社会做出贡献。那时的想法还很朴素,那时还有美好的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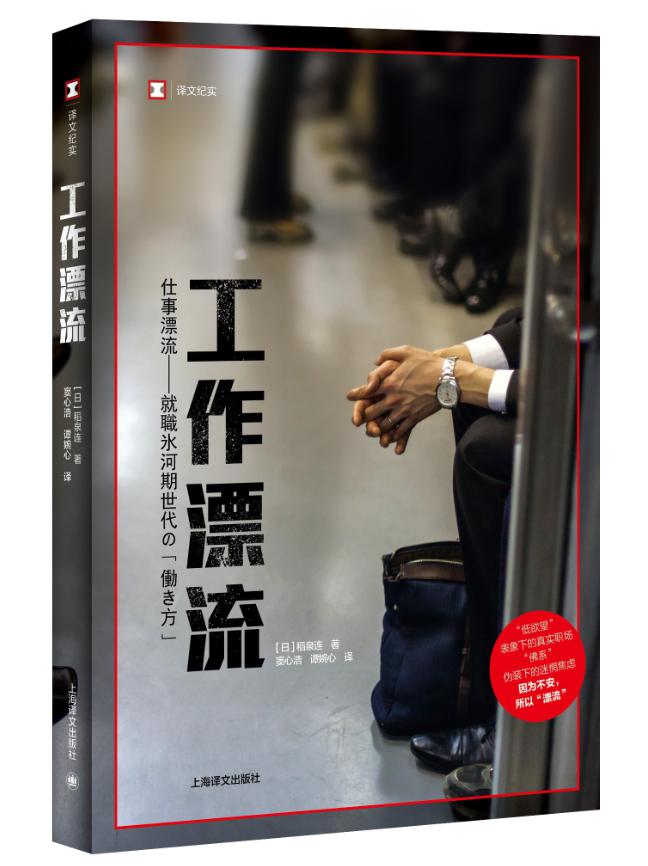
编辑:任思蕴
来源:摘自译文纪实系列《工作漂流》 (日)稻泉连 著,窦心浩 谭婉心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