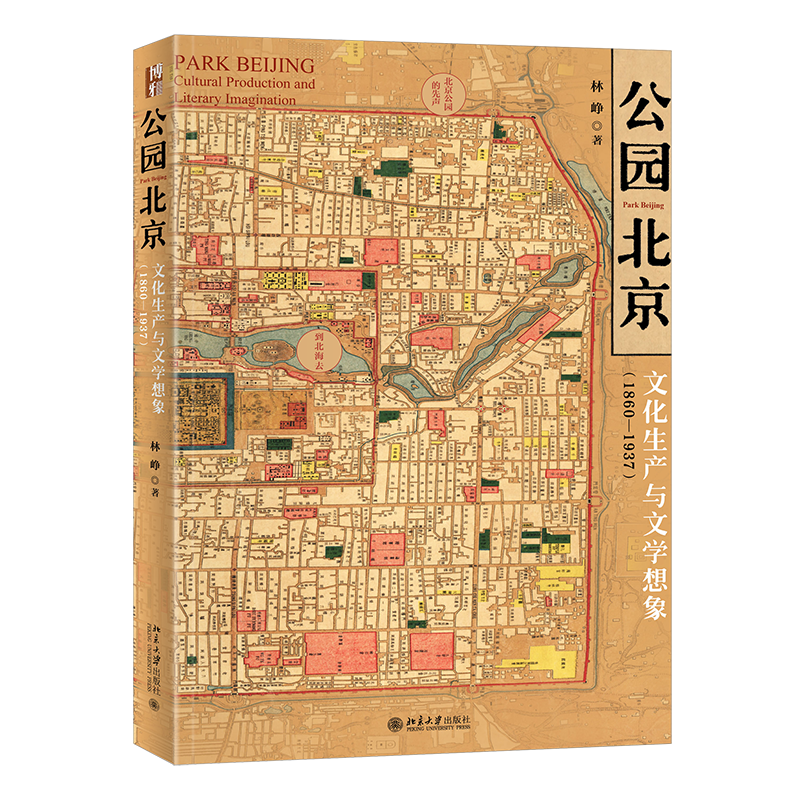
《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
林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研究内容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园,既包括清末民初政府正式建造、开放的公园,也包括具有公园性质的公共游览空间,借此折射清末民初北京的现代性转型。
>>内文选读:
后记(节选)
十年前,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我赴哈佛大学访学,着手北京公园的研究,起手写的就是“世界人的乡愁”,这部分最后成为了本书的附录。在我当时的笔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第一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以“大地各国园林”皆为我所有、四海为家的气魄,不能不说某种程度上投射了个人意气风发的心态。十年后,我再赴哈佛访学,为即将出版的书稿撰写后记。当我翻看自身多年前所论述的康有为在“国人”与“世界人”的身份认同之间往返挣扎,尤其是康有为自剖心迹的“临睨九州,回头禹域,则又凄怆伤怀。故乡其可思矣,亦何必怀此都矣”等语,不由心有戚戚,感慨万千。十年一觉,大梦初醒,恰好为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画上一个圈。
我们这一代中国“80后”大多有儿时学校组织赴公园春秋游的经历,列队去福州小西湖改建的“西湖公园”,归来还要统一写作文,是福州小学生每年的例行公事。而我自小长大的家毗邻福州的“温泉公园”,迄今假期归家,我依然会保持饭后与母亲赴公园散步的习惯,“红歌大家唱”和广场集体舞更是母亲每晚的保留节目。当时的我尚不明了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空间背后所蕴含的深意,但私人的感性经验,却使我对于公园始终怀有天然的敏感和亲切。
现在想来,这两个公园其实分别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典型的公园模式:前者是将既有的中式传统园林开放,后者则是另起炉灶的西式绿地公园。同时,上述对于公园的两种使用方式——青少年的春秋游,与中老年的广场舞,实际上都与共和国时期对于公园作为“人民的公园”之蓝图息息相关。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常遇到同行学者或关心或怀疑地问我:为什么要做公园研究呢?也许正是这些切身的经验,令我深刻地体认到,这种不为宏大叙事所关注、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空间与生活的实践,却在人们实际的生命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我尝试做的,恰是打捞这些历史缝隙日常生活的碎片,复原历史的丰润和幽微之处,追问物质空间对于精神世界的意义。
北海公园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个人气质是偏于“现代”的,这大概也奠定了我看待北京的眼光。在台湾访学时的指导教授刘人鹏老师曾对我说,她对北京最失望的是什刹海一带,惋惜商业因素的引入破坏了南锣鼓巷、烟袋斜街这些老胡同原汁原味的北京风情。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所谓“原汁原味”的老北京何尝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读书时我曾选修陈平原老师的城市研究课程,最后一堂课要求我们借一张图、一首歌、或一个小物件之类诠释自己对于北京的印象。我选了一张照片,是烟袋斜街对面一条不知名的小胡同。很不起眼的破败小巷,深处却张挂着许多朋克风格的招牌,上书英文字母Tattoo(即刺青),衣着入时的摇滚青年与推着代步车的老大爷,相映成趣。非常奇妙的拼贴,却又那么自然而然,毫不生硬。
我认为,这正是北京的神奇之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老古董,我们也不应把它作为一个静止的博物馆;它既不是完全旧的,也不是完全新的,而是充满了包容与张力,其老躯壳里很可能流淌着最新鲜的血液。本土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彼此相安无事,各得其所。这也是我理解近代北京公园的起点。
作者:林峥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