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由于周作人身体力行的揄扬鼓吹,安徒生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绝大部分译本都像周作人所期盼的那样使用白话,可惜尚未能娴熟自如。为了不至于让读者对外来童话产生过多隔膜,有的译者还做了一些归化改造。依据不同读者的实际需求,有些译本还做过相应的删改。
丹麦作家安徒生毕生创作了160多篇童话,自晚清民国之际逐渐传入中国,引发了读者持续不衰的热情。个别作品如《皇帝的新衣》,更是由于诸多机缘,激起了许多人的勃勃兴致,不断地进行推介、翻译、摹仿、新编、探源和比较。今人对此虽然稍有论列,但或辗转承袭而不无讹谬,或语焉不详而多有阙略。仔细钩沉排比相关史料,不仅能够藉此考索晚近以来文学观念的递嬗演进以及学术风气的蜕变流转,更能引导我们深入窥探在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心态。
最先向国人介绍安徒生的是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孙毓修,他从1909年起主编《童话》丛书,第一集内就包括《海公主》(即《海的女儿》)、《小铅兵》 (即《坚定的锡兵》)等安徒生作品。他还陆续发表评论,频频述及其人其作。如在《读欧美名家小说札记》(载1909年《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一期)中介绍道,“安徒生Anderson者,丹麦人也,以说平话闻于时,著Fairy Tales。人人诵习,至今不废”,“恒喜以诙谐之辞,强小儿而语之,使闻者不懈而几于道。其感人之速,虽良教育者不能及也”;在《神怪小说》(载1913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四号)中则将他誉为“丹麦之大文学家,亦神怪小说之大家也”,“其脑筋中贮满神仙鬼怪,呼之欲出,是诚别擅奇才者也”;随后又在《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载1913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六号)里进一步指出,“安徒生之书,时而花妖木魅,时而天魔山魈”,“当其闭置一室,凝神静思之顷,不啻变其身为神怪”。虽然并未言及《皇帝的新衣》,也时有牵强比附,但这些意见还是成为后人评述时的重要参照。
紧随其后,周作人发表《童话略论》(载1913年《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八册),尤为强调:“著作童话,其事甚难,非熟通儿童心理者不能试,非自具儿童心理者不能善也。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Anderson为最工,即由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故能如此。”尽管未暇详加论说,可敬慕之情已溢于言表。只是或许受到绍兴方言的影响,将“Anderson”译作“安兑尔然”,不免让后来的读者略感陌生。他稍后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载1913年《叒社丛刊》第一期)中有更为翔实的评议,在胪列作品时特别提到了《皇帝的新衣》:“言皇帝好衣,有二驵侩言能织美锦,举世无匹,唯下愚之人或不称其职者视之则不能见。帝厚偿之,使制衣。二人张空机作织状,使者往视,见机上无物,而不敢言,唯返报盛称其美。帝亲临检,亦默而退。及衮衣已成,二人排帝使裸,加以虚空之衣。皇帝乃从百官,警跸而出。观者夹道,见帝裸行,咸莫敢声。安兑尔然于此,深刺趋时好而徇世论者。”鲁迅在当时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又得二弟信,附安兑然卮言二篇。”(《壬子日记》1912年10月12日,《鲁迅全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可知周作人正尝试翻译安徒生童话,并和兄长有过交流切磋。此处虽然只是撮述概要,但已经粗具始末,一些特定译名如“驵侩”,也和他数年后正式发表的译文一致。鲁迅对此看来也很有兴趣,日后在杂文里还涉笔成趣地提到过“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
偏爱安徒生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对相关评论也有所关注。数年后,周瘦鹃将编译的英文小说修订汇编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华书局,1917年),其中有安徒生(周氏译作“盎特逊”)的一篇《断坟残碣》。正文前另有《盎特逊小传》,传末总结说:“综其生平著述,以神怪及寓言小说为多,而意中皆有寄托,非徒作也。有《丑鸭》‘The Ugly Duckling’(此篇夫子自道)、《锡兵》‘The Tin Soldier’、《皇帝之新衣》‘The Emperor’s New Clothes’、《火绒箱》‘The Tinder Box’诸篇,篇幅虽短,寓意却深,其状物写生,绝富兴趣,欧美儿童佥好之。”“神怪”之论无疑承袭自孙毓修,但已明确将《皇帝的新衣》视为安徒生的代表作,称道其言近旨远而妙趣横生的特色。《丛刊》出版不久就引起早年编译过《域外小说集》的周氏兄弟的注意,为此特意撰写评论(载1917年11月30日《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五期,原无署名;后拟题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收入《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尤其表彰此书“每一篇署作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对那段针对安徒生的评介应该也极为认同。——附带提一下,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中回忆,鲁迅看到《丛刊》之后,“很是欣慰,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见该书第四分《补树书屋旧事》第十二则《办公事》);而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中则说,鲁迅将该书“带回会馆来,同我会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见该书《鲁迅与清末文坛》篇)。《鲁迅全集》在编辑时根据前文将此篇归入鲁迅名下,却丝毫不提后文,恐怕有些欠妥。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问世后风行一时,对安徒生的大力推介自然会引发读者的好奇。没过多久,陈家麟、陈大镫合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中华书局,1918年)就应运而生,选译的六篇中恰有《国王之新服》,这也是这则童话的首个完整汉译本。两位译者与中华屡有合作,因而出版方在宣传时不遗余力,在《本局出版各种小说提要》(解弢《小说话》附录,中华书局,1919年。从题名看,《提要》应是中华书局所拟,今人多误以为解氏手笔)中,除了概述全书内容外,还提醒读者留意,“其最奇之两篇”,一为《牧童》,“一为《国王奇服》,国王既好奇服,有二织工献织无形之衣,衣惟忠智者见之。
国人惧受不忠不智之名,均诡云见衣。于是国王乃著无形之衣,裸体游于国中”,予以郑重推荐。而强调其构思的新奇不凡,大概也道出了译者的择取标准。
然而《十之九》并没有令所有读者感到满意,“凡外国文人,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的,多是不幸。其中第一不幸的要算丹麦诗人‘英国安得森’”,周作人在《随感录(二十四)》(载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又改题为《安得森的〈十之九〉》,收入《谈龙集》,开明书店,1927年)开篇就略带戏谑地发难,原因是此书竟将作者署为“英国安德森”(周氏误记作“安得森”)。想来译者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未予细究便想当然地断定作者来自英伦。不过这并非绝无仅有的误会,上述《本局出版各种小说提要》也同样说“原著者英国安德森”;而赵景深还调侃过某戏院的广告,居然称安徒生为“德国文学家”,“陈家麟等的《十之九》曾请他老人家硬入了英国籍,现在百星大戏院又逼他改入德国籍了。英、德本为世仇,不知安徒生在泉下当作何感想,怕不左右做人难也”(《安徒生的玻璃鞋》,载1929年《文学周报》第七卷),足见当时对安徒生的了解仍然多有隔膜。如此敷衍草率,在“自认是中国的安党”的周作人看来,当然忍无可忍。经过仔细比勘,他对译笔也多有诟病,如文辞过于古奥,“把小儿的言语,变了八大家的古文”;内容也时有舛误,“删改原作之处颇多,真是不胜枚举”。覆核原书,都不算求全责备的苛论。比如书名当取自《庄子》的“寓言十九”,尽管古雅别致,可和原著并无关联,对普通读者而言也略嫌艰涩。至于向壁虚构的内容,更是层出不穷。如《国王之新服》中说国王“又派一大臣,曾为国杀子,不可谓不忠;曾入海算沙,不可谓不智”,“为国杀子”典出《左传》,“入海算沙”源于《景德传灯录》,都是译者添油加醋的笔墨。如此无中生有,和周作人指摘的另一例——“小克劳思骗来的牛,乃是‘西牛贺洲之牛’”——简直如出一辙,“这岂不是拿著作者任意开玩笑么?”
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逐一指摘各篇译文,却唯独没有涉及《国王之新服》。这大概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增订校阅《域外小说集》(上海群益书社,1921年),书中也收有“丹麦安兑尔然著”《皇帝之新衣》。与《十之九》相较,虽无凭空生造之弊,可依然使用文言来翻译,遣词造句也就不免多有迁就。如叙及皇帝率领群臣前往巡视,“朝臣环视久久,亦无所见,唯皆赞叹曰:‘锦甚美!’又请帝制以为衣,日内大酺,当有行列,可御以出。众皆大悦,称锦美不绝声。帝于是赐驵侩以武士勋章,悬诸衣纽,又进职为织造大臣,锡号曰织科学士”,非但“织造大臣”“织科学士”戏仿了古代职官名号,“大酺”“驵侩”“锡号”等词汇也稍显生僻。周作人对此心知肚明,在《域外小说集序》里并不讳言,“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按:原文为誳)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并坦陈“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既已如此,当然不便“五十步笑百步”地再去讥嘲别人。增订本《域外小说集》另附有《著者事略》,轮到安徒生时说:“安兑尔然天禀殊异,老而不失童心,故绌于常识而富于神思。其造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庶类,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天成,殆臻神品。词句简易,如小儿语,而情思亹亹,喜乐哀愁,皆能动人,状物写神,亦入妙境。”对其运思命笔赞不绝口,尽管并未特指,可既然只选译了《皇帝之新衣》,显然认定此篇最能彰显作者才情。他接着又评论道:“唯转为华言,即失其纯白简易之长,遂不能仿佛百一。近有译者,言是搜神志怪一流,则去之弥远矣。”一方面希望后来的译者能够如实传达原作的风神情韵,另一方面则将矛头直指孙毓修,认为“神怪”之类的断语有悖事实。此后还有译者对此再予驳正,正如陈敬容所言,安徒生童话“虽然想象极其丰富,但又极合人性”,“并不是徒涉虚玄,或者完全流于神怪”(《丑小鸭·译者序》,骆驼书店,1948年)。可见随着译介工作的不断深入,最初的肤廓印象也会逐渐得到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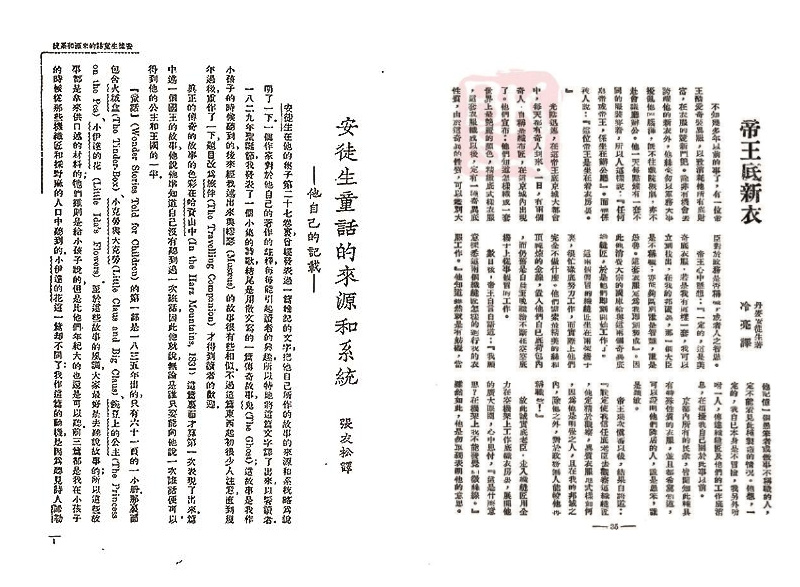
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他自己的记载》(左),冷亮译《帝王底新衣》(右)
由于周作人身体力行的揄扬鼓吹,安徒生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顾均正在翻译《水莲花》(开明书店,1932年)时就说:“自从周作人先生在《新青年》上介绍他的作品之后,就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他的童话,陆陆续续有人在各种报章杂志上翻译出来。”其中也包括多种《皇帝的新衣》译本。有些译者直接受到周作人的启发和引导,如赵景深先后翻译过《国王的新衣》(载1920年《少年杂志》第十卷第十二号)等作品,并汇为《安徒生童话集》(新文化书社,1924年),在《短序》中便致以谢忱:“我们的大孩子周作人先生对于我《安徒生童话集》的编印,有莫大的勉励。他十分的期望这本书出版,并为我筹画应该选译的篇名。”有些译者则参考借鉴过周作人的译文,如樊仲云翻译的《皇帝之新衣》(载1922年《中华英文周报》第八卷第188、189期》)将骗子译作“驵侩”,就沿用了周氏的译法。与此同时,相关评论的不断引介,也会促使人们将目光逐渐集中到《皇帝的新衣》之上。张友松翻译的丹麦评论家Boyesen所著《安徒生评传》(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八期)评论道:“在我看来,全部里最可宝贵的要推《皇帝的新衣》(The Emperor’s New Clothes),那种用意的新颖,和所指摘的情形之普遍,真是拿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湮没不了它的特长。世人对于社会上一般人的意见之尊重,和所谓‘习尚’之严酷制人——这些事受人讥评,从没有像这篇这样的又确切又诙谐。”对其立意的新奇深刻和内容的幽默诙谐推崇备至,想必会令众多译者跃跃欲试。当然,由于不同译者水平高下有别,翻译理念互有出入,所据底本又各不相同,所以译文质量也就难免参差不齐。

赵景深译《安徒生童话的艺术》和《皇帝的新衣》
绝大部分译本都像周作人所期盼的那样使用白话,可惜尚未能娴熟自如。荆有麟翻译的《王的新衣》(载1925年《民众文艺周刊》第11号),说起骗子装腔作势的场景,“他们竖起两架织机,做作的形容,仿佛他们在那作工,可是织机上边是没有一件东西的。在要求上他们虽然是很热心,要求那美丽的绸绢和最好的黄金,可是这些个东西他们都把它放在自己的衣袋而空虚的在织机上工作,并且还作到很深的夜里”;冷亮翻译的《帝王底新衣》(载1933年《艺风》第一卷第五期),提到国王准备一探究竟,“他知道虽然就是有妨碍,当他记忆一个蠢笨者或做事不称职的人,定不能看见此种制造的情况。他想,一定的,我自己本身是不冒险,我另外吩咐一人,传达织缝匠及他们的工作底消息,在烦扰我自己关于此事之前”,尽管都还不算太过费解,可总觉得生硬拗口,让人联想起鲁迅在翻译儿童文学时的感慨:“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小彼得〉译本序》,收入《三闲集》)受到原文制约的翻译比起单纯的创作来,显而易见更容易顾此失彼而左支右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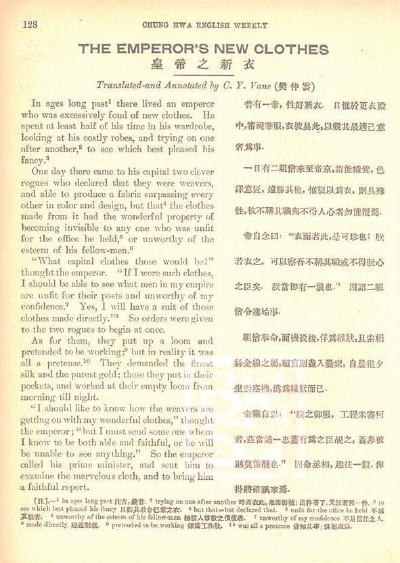
樊仲云译《皇帝之新衣》
为了不至于让读者对外来童话产生过多隔膜,有的译者还做了一些归化改造。步揆翻译的《皇帝的新衣》(载1924年《兴华》第二十一卷第二十六期),说起第一位大臣奉命探察,“老丞相眼光在眼镜里透出来说道:‘漂亮呀!可爱得很!这样的花纹颜色好极了!我一定要告诉皇帝说我很满意这美锦!’两拐子说:‘我们听你这样说,欢喜得很。’”与此类似的还有甘棠翻译的《皇帝的新衣》(收入甘棠译述《安徒生童话》,商务印书馆,1934年),将这位大臣译作“老宰相”。毋庸赘言都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才会采用“丞相”“宰相”“拐子”等译法。斐成翻译的《皇帝的新衣》(载1927年《儿童世界》第十九卷第十九期),讲到皇帝外出巡游,“最后一个小孩发锐声喊道:‘真有趣呀!那皇帝头戴金冕,足登粉靴,却只穿了衬衫,并没有着上龙袍!’”不厌其烦地将原作中简洁明快的一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敷演铺排了一番,连续用了 “金冕”“粉靴”“龙袍”等本土读者耳熟能详的服饰名称。虽然脱离原文较远,但阅读时的亲近感肯定油然而生。
依据不同读者的实际需求,有些译本还做过相应的删改。樊仲云精简过许多内容,如开篇时译作:“昔有一帝,性好新衣,日惟于更衣殿中,审视华服,衣彼易此,以观其最适己意者为事。”只是略陈梗概而已。这是由于他采取中英对照的形式,本意在指导初学者研习英语,原作的英译已经删繁就简,所附的汉译也唯有亦步亦趋。赵景深在最初翻译时对结尾做过删节,说到众人齐呼“国王身上一件新衣服也没有!”就戛然而止,兴许因为这原先是说给妹妹听的睡前故事,“讲到后来,我不知自己是讲的什么,我便睡熟了,伊也许也早已睡熟了”(赵景深《安徒生童话集·短序》)。数年后他修订译文(收入赵景深译《皇帝的新衣》,开明书店,1931年),才补上了原来的结局。范泉翻译的《皇帝的新衣》(收入范泉编译《安徒生童话集》,永祥印书馆,1948年),为了便于小读者能在课余读到更多名著,同样做了不少压缩。比如安徒生在介绍皇帝的喜好时,有一通夸张戏谑的描写:“他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衣服。正如人们一提到皇帝时不免要说‘他在会议室里’一样,人们提到他的时候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据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就被删削殆尽,情节虽然变得更为紧凑,但也损失了不少摇曳多姿、妙趣纷披的神采。

安徒生的作品素以明白晓畅著称,然而仔细比对各家译文,仍能发现在理解时偶有异同。比如当小孩子一语道破真相后,荆有麟译作“——呵天,听候赦罪的声音罢。这父亲说着”;冷亮译作“‘谛听天真烂漫底忠告!’他的父亲请求说”;步揆译作“他的父亲说,‘哎呀,听听这小孩子’”;而叶君健译作“‘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即便同一位译者,前后也会有变化,如赵景深一开始译作“他父亲骂他道:‘好不晓事!’”后来则改为“父亲说:‘这孩子好不晓事!’”面对孩子的童言无忌,这位父亲究竟是胆颤心惊,还是痛切斥责,抑或是鼓励有加,几乎让读者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早期诸家均据英、日译本转译,至叶君健才依照丹麦文翻译,公认最为确切,无疑最可采信。不过此处表述本来就比较含蓄,不同译者或受底本影响,或据个人体会,仔细寻绎其言外之意,由此产生分歧也是翻译中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
作者:杨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李伶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