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寅恪的史学带有文化史学的特点,其选题论域之要旨,实在我国古代的思想和制度。”——《陈寅恪论稿》
“陈寅恪的史学带有文化史学的特点,其选题论域之要旨,实在我国古代的思想和制度。”——《陈寅恪论稿》
马一浮也是影响我至深的学术大师,相比之下,他的影响表现为潜移默化,缓慢地润入心田,陈寅恪则是隆隆作响的震撼。所以如此,是由于陈寅恪的学说有一种志不可夺的力量。
我研究陈寅恪迄今已二十有五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出了三本书:一是《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2年故宫出版社出版;二是 《陈寅恪的学说》,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三是本书,《陈寅恪论稿》,仍为三联出版。书中的篇章文字系陆续写成,也大都在学术刊物和报纸的学术版刊载过。只是整理成书是最近几年的事。因为同时也在研究其他课题,所花时间比研陈多得多。单是研究马一浮就持续十有余年。由研马而进入宋学,旁涉佛学,又返归六经,时间更无法计量。何况还有多年来一直关注的国学,以及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一些课题。
这种多头并进的研究方法,好处是不致忘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而为一隅一曲所局限。不好处是,战线长,论域多,出书慢。以至于一度常不自觉地诵念一副对联:“终年著述无一字,大患分明有此身。”当然也和六十初度时生了一场大病有关。熟悉我研究状态的一位友人,一次打来电话,问又叉到哪儿去了。我说马一浮。他大笑,并问何时回来。显然指的是回到陈寅恪研究。所幸无论我走到哪里,陈寅恪的思想和精神,都不离不弃地跟随着我的行程。古今东西的大师巨子,很少有像陈寅恪这样,因读其书而受到透彻的精神洗礼。马一浮也是影响我至深的学术大师,相比之下,马的影响表现为潜移默化,缓慢地润入心田,陈则是隆隆作响的震撼。所以如此,是由于陈寅恪的学说有一种志不可夺的力量。“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试想这是怎样的情致,何等的力量。百年以来的现代学者中,没有第二人能够与陈寅恪的这种精神情致相比肩。
《陈寅恪的学说》一书,主要是梳理和还原陈氏学说体系的内在结构,提出陈寅恪不仅是大史学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体系的构成,一是属于义理学维度的种族与文化的学说,二是属于考据学范畴的陈氏阐释学,三是属于词章学方面的佛典翻译和文体论。此三方面的内容构造和研究旨趣,我在《学说》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三个章次,作了重点分论与阐释。余者第一章为探讨陈氏学说形成的个人经历和家世背景,第二、三章是还原其博学兼通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第四章系阐明“中西体用”的文化态度在学说建构中所起的立基作用。最后的第八章,章题为“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意在总括其秉持一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何令陈氏学说闪现出照彻人文学领域的永恒之光。也许这就是此书出版后,一直受到读者青睐的缘由吧。
《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则是对义宁之学的一个专项研究,尽力在汇拢爬梳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再现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其子陈三立的襄助下,引领和推动1895至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过程,以重构当时从朝廷到湘省的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和当事人的心理结构。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叙论陈宝箴膺任湘抚前在季清社会所扮演之角色,是为前论部分。第二至第六章叙论湖南维新运动的举措和展开。第七章和第八章论述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和挫折,以及因慈禧政变而遭遇失败。此七、八两章是为该书的高潮部分,时局的跌宕变换所导致的人物关系的重组和当时人的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此两章有具体而微的呈现。最后的第九章,特为考证陈宝箴死因而作,长四万余言,是《新政》篇幅最长的一章,有关陈宝箴系慈禧密旨赐死的任何蛛丝马迹的线索,都鲜有放过。后来吾友陈斐先生又补充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新材料,使得此一疑案不致再有他解。此一悲剧事件,对陈氏家族的打击极为沉重,不止陈三立首当其冲,大病几死,当时只有十岁的未来的史学家陈寅恪也受到心灵的巨创。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陈寅恪论稿》,在性质上可作为《陈寅恪的学说》的姊妹篇。如果说《学说》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内部构造的疏解,《论稿》则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外部学术触
点的著论。《论稿》第一章“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如题义所示,是为研究其家学传统和学术渊源,《陈宝箴和湖南新政》的首章与此篇之第一节有所重合,其余则完全不同。此章的特点,一是引用所能见及的有趣的资料,补论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郭嵩焘的知遇与交谊;二是对义宁之学的渊源和学术宗主有独家的阐发。我发现,从陈寅恪的曾祖父陈琢如开始,到祖父陈宝箴,到父尊陈三立,都一以贯之地宗奉阳明之学。此节文字曾在1994年9月举行的“阳明心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刊于2001年第2期《读书》杂志。被当代阳明学的护法蒋庆兄推举为首创斯义。全文则刊载在2002年《中国学术》第3期。收入本书前,又经过两次改订增补,第四节“陈宝箴的阅历陶镕和志行名节”和第五节“义宁之学的诗学传统”,均为后来所增写,文字也由当初的两万字扩充至三万字。陈寅恪一再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从陈宝箴、陈三立的志行名节中找到家世信仰的熏习源头。
《论稿》第二章《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是对陈寅恪诗作的研究。义宁之学本来包含有诗学部分,第一章对陈宝箴和陈三立的诗作,已有所评骘。散原固是同光诗坛的翘楚,而其诸子亦皆有诗传,尤其寅恪先生之诗作又自不同。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著《寒柳堂集》,附有 《寅恪先生诗存》,所收陈诗远不完善。199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诗集》,是为当时汇辑陈诗最称完备的文本。细详之下,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家国”、“兴亡”、“身世”、“乱离”这些语词,反复出现于《诗集》之中,似有一唱三叹之致。于是作了一次研究取样,从《诗集》里找出包含有“家国”的诗句八例,“兴亡”二十一例,“身世”九例,“乱离”八例。并发现寅恪先生1965年写的《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具有特殊的题旨义涵,特别其中的“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两句,可以看做是陈寅恪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以此,才以《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为题,撰写了此章文字,始刊于《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出版,之后虽经《光明日报》选载一个整版,看到全文者实甚少。但在《陈寅恪诗集》出版当年的8月16日,清华大学曾开过一次《陈寅恪诗集》学术座谈会,我应邀出席,并在发言中就陈诗中的“家国”、“兴亡”等四组关键词作了取样说明,大家甚感兴趣。周一良先生与会,他对我的研究表示认可。文章写就十年之后,即2014年,又对此稿作了一次增补,收入本书的此章即为增补后的文稿。
第三章《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写于2006年7月,首刊于《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意在对义宁之学的八个骨立之点,作一次论纲性质的归结说明。其中第四节“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是为第一次提出,被心系义宁的一位友人誉为概括精准。而第八节“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则是对论陈诗章的补充论证。当我反复诵读寅恪先生诗作的时候,分明感受到作者有一种深层的哀伤充溢于字里行间,以至于不断有哭泣、吞声、泪流的诗句,反复出现于《诗集》之中。我作了一番统计,发现此类诗句竟有二十六例之多。而任何“哀伤”都与已往的记忆有关。对陈寅恪而言,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在戊戌政变中遭受的打击,包括两年后祖父被慈禧赐死,是无法忘怀的记忆。作为史学家,他自然还会想到,假如当年的维新变法能够按义宁父子的稳健思路行进,就不致有后来的越出越奇的无穷变乱了。所以他越思越痛,痛上加痛,便不由自主地写下了“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等直接发慨抒愤的诗句。陈三立《散原精舍诗》中,也有诸多“家国”并提的抒怀感发之诗句,我从中找出“百忧千哀在家国”、“旋出涕泪说家国”、“十年家国伤心史”等近二十组诗,每首都不离“家国”。本章之撰写,开辟出义宁之学研究的新思路,使笔者往寅老精神世界的深处又递进了一步。
第五章是对陈寅恪晚年的大著述《柳如是别传》的专项研究。此章文字最早的稿本写于1989年的年底,《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刊载。十年之后的2001年5月,“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和历史写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我应邀出席此会并以《“借传修史”: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为题,作为提交和在会上报告的论文。这是在原稿基础上,经过改订重写过的专篇论著,篇幅亦扩充至近三万言。研究义宁之学,再没有比对《别传》的评价更分歧的了。老辈如钱锺书先生、李一氓先生,都不特别看好此著。我的看法大异与此,而是认为《柳如是别传》是寅老一生最重要的著述,其学术目标则是“借传修史”,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这一看法当1989年撰写此文的初稿时,就明确提出来了。后来,随着自己研陈的逐渐深入,持论益坚。一次在答友人论《别传》的信函里写道:“我对《别传》评价极高,认为那是大史家一生最重要的著述,其史法、义蕴、体例,可视为近代以来史著的最高峰。无人能比,无人可及。斯为‘借传修史’之创体,所修者盖明清文化之痛史,亦思想之史、政治之史也。寅老一生心事学思尽在《别传》一书中。”职是之故,此章在本书中的地位,应居于特别之位置。
第六章的《陈寅恪与〈红楼梦〉》,写于2000年,刊载在2001年《文艺研究》第一期上。此章的写作由头,是缘于陈寅恪与红学家俞平伯的关系。他们初交于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园。寅恪先生请俞平伯为之书写韦庄之《秦妇吟》,平伯先生请寅恪为其祖父俞曲园的《病中呓语》撰写跋语,所谓倾盖之交,由此开始。因之,当1954年俞平伯遭受无妄之灾时,寅恪先生禁不住发声了。这些故事由于缘合于笔者的研究范围,禁不住手痒,便撰写了此文。连带也将寅老在各种著述中随手援引《红楼》故事以为参证的例子,一并搜罗起来,加以贯串论说,使得此文读起来应饶有趣味。巧合的是,台湾大学的刘广定教授,我的多年的好友,也写了一篇同题论文。题虽同,引例也难免重合,但写法绝无重合之处。恰合于寅老在《论再生缘》中所说的,他与陈援庵先生抗战时期人各一方,所考证杨玉环“入道年月”,结论竟“不谋而合”,但“两人俱无抄袭之嫌疑也”。广定兄的文章收入其《化外谈红》一书时,附记了此一往事(刘广定著:《化外谈红》,台北大安出版社,2006年,第34页)。“化外”者,盖由于广定先生是研究化学的专家,以此自谦也。我此次将《陈寅恪与〈红楼梦〉》编次收入本书,内容又作了许多增补,特别《论再生缘》中的涉《红》部分,系重新写过。因此该章之呈现,可以说是既为旧观亦非复旧观了。
第七章《陈寅恪与王国维和吴宓》,初稿成于1992年,开始陈吴单独成篇,曾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后来《吴宓日记》正、续编出版,有了更多的可资依凭的原始资料,于是经修改、增补,又于2013年重新定稿,在《中国文化》2013年秋季号刊出全文。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王、陈的关系自是不同一般,故陈的《挽词》以“风义生平师友间”状之。而吴宓则是陈的终生契友,亦为静安先生所信任。王遗嘱:“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可见王、陈、吴三人关系之全般。此章之作,盖为研陈所不能少。
第四章《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是为新写,两月前方竣稿,还没有发表过(《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一稿,蒙《中华读书报》编者慧识,破例以三个整版的篇幅于2016年9月14日刊出,在此特表谢忱)。但此章的重要,在于此题未就,《陈寅恪论稿》便没有资格出书。我一再申论,陈寅恪的史学带有文化史学的特点,其选题论域之要旨,实在我国古代的思想和制度。于魏晋主要是思想研究,于隋唐主要是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研究。拙稿《陈寅恪的学说》第五章于此义阐论较详,并就种族与文化的关系揭示义宁学说的学理发明。本章今次对斯义又有所补论。更主要的,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干儒、释、道三家都有极明晰的断判,于儒家则说:“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于佛教则说:“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于道教则说:“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弹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于三家综论则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笔者固陋,不知海内外之学人还有谁何之论三教,能有如是之创发明断而又深具历史哲学之义涵。因此不得不收视凝心,固化一段时间,专门撰写此章,以补前此之所未及者。此章写就,则《陈寅恪论稿》可以付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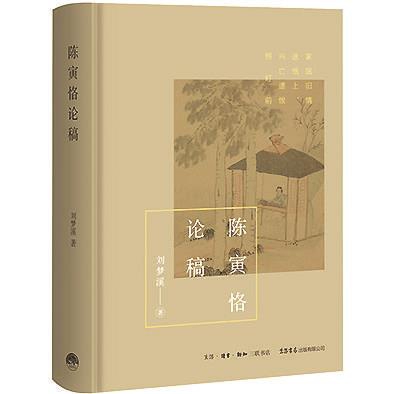
附录之两篇文字,一是《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新释,一是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的诠解,都单独发表过。因与书中有的章次不无重合之点,故以附录的形式单存另列。(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本文为《陈寅恪论稿》序)
作者:刘梦溪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