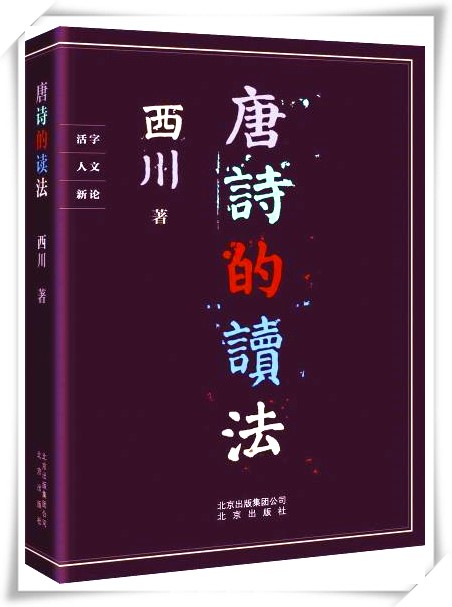
▲《唐诗的读法》 西川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西川新作《唐诗的读法》,口袋书的体量,讨论的问题却很深、很大,细究起来,写个大部头也未必兜得住。但西川举重若轻,几乎谈笑间就把问题讲清楚了,还讲得妙趣横生,让人读着充满了愉悦感。
那他到底讨论了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唐诗生长在什么样的土壤里。我用了“土壤”,而不是“背景”,理由是,背景这个词容易产生隔离感。好像唐诗是便签纸,被一张张贴在背景墙上,到头来诗是诗,墙是墙,并无内在关联。而实际上,诗歌应该是生长出来的,从诗歌的土壤里生长出来。
现实的土壤会变化,诗歌的土壤同样如此。这是西川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这件事何以重要?因为其中隐藏着唐诗,乃至中古之后传统文学的密码。
我们知道,从北魏到隋朝再到初唐,政权一直掌握在关陇集团手里。因此有学者认为,隋亡唐兴的实质,不过是关陇集团内部对权力格局进行的再调整。无论此说能否站住脚,初唐的高层官员多为关陇权贵,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养成了一群政治贵族,书法家褚遂良、宫廷诗人上官仪,即为代表人物。而政治贵族创造的文化,自然是贵族文化。
在唐代,家庭出身和姻亲关系十分重要。关陇权贵将官位、爵位在本集团内相授受,子承父业、兄终弟及成为常态。这就是所谓的“恩荫制度”。然而情况悄然变化着。武则天在发迹过程中,面对阻碍其上位的关陇权贵,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直接打击,杀长孙无忌,杀上官仪,废长孙皇后,震慑朝野;二是放开科举,大力提拔寒族子弟,以制衡关陇权贵。
寒族子弟得以登上庙堂,凭的是皇恩和才学,对靠裙带关系占据高位的贵族,充满了鄙视。而贵族也瞧不上这些年轻士人,觉得他们举止轻浮,形同暴发户。于是人以群分,形成了贵族群体和士人群体这两大势力。双方在政治领域勾心斗角,在文化领域互相拆台,斗争愈演愈烈,贯穿了大半个唐代。
大凡一个群体,总要设定若干身份标识,拥有这些标识,才会被接纳为“自己人”。士人群体的身份标识之一就是“诗”。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杂文”(指诗赋)占有重要位置,尤其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写诗作赋已经是士人的基本功。反过来,会不会写诗,写不写得好诗,就成为判断你是不是士人的标准。因此对唐代士人来说,写诗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活动,参加科举考试得写诗,想获得大官垂青得写诗,送别友人得写诗,文人雅集得写诗,为人祝寿得写诗……翻一遍《全唐诗》你会疑惑,其中不少作品明明很平庸啊,细瞧原来都是应酬之作!
现代人忘了这层关联,把《唐诗三百首》当作唐诗的完整风貌,以为唐代士人时时灵感奔涌,金句张口即来。其实《唐诗三百首》是披沙拣金的成果,只占《全唐诗》的极小部分。而唐代士人的日常性写作,就像前面说的,目的多为应酬,这种程式化的写作并不怎么需要灵感。西川发现,士人们会携带“随身卷子”,以备不时之需。随身卷子上记录着“古今诗语精妙之处”,且分门别类——哪些是描写春天的,哪些是抒情雪景的,刮风下雨又该说些什么,都设计好了。事到临头拿出卷子查阅,总有一款合适,再也不用担心词穷了。
诗歌要遵循格律,要用典,而且规范越来越严格、精细,也是从唐代开始的。同样,这也不只是艺术发展的要求,士人们是用近体诗构筑壁垒,排斥异己,加强身份认同。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格律,写得再好也是打油诗、顺口溜;不懂典故,无法同士人唱和往来。这样,你就被划在士人圈子之外。
从这个角度观察唐代的诗坛生态,就相当有意思了。例如,李白与王维是同龄人,又都名满天下,可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交往。为什么呢?因为王维是贵族,左右宫廷诗歌的趣味;李白则出身草莽(寒族),摆出一副非主流的姿态挑战权威。而从诗风看,两人也是千差万别。有理由推想,李白和王维互相看不惯,但终究没撕破脸皮,各自保持着微妙的沉默。

聊完八卦,再来讨论唐诗的写作对象,即,这些诗是写给谁看的?肯定不是民众。民众搞不清“三连平”“犯孤平”这类近体诗禁忌,更无法欣赏不知从哪儿挖出来的生僻典故。西川的结论是:格律诗是“同等学识、相似趣味的士子、进士们之间的私人交流”。
有人可能会问:那白居易呢?他不是深切地同情劳苦大众吗?西川回答:他是同情,但他的这种同情,是要说给元稹、刘禹锡等同道听的。进一步的,可能还想说给皇帝听。这由白居易的身份(官僚地主)所决定。“白居易是居高临下的人。他诗歌中的日常有限性、私人叙事性、士大夫趣味、颓靡中的快意、虚无中的豁达,根本不是当代人浅薄的励志正能量贺卡填词。”说到底,白居易还是典型的士人,他对老百姓的同情,是居高临下的士人式同情。
这就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读懂唐诗了吗?如今不少人热衷古诗词,特别爱玩接龙似的背一大串金句。这本来无可厚非。毕竟对普通人而言,文艺是用来装点生活的,让平庸的日常变得美好一些(所谓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不过,如果真以为如此就能和古人对话,深入古典作品的内核,则未免托大了。
黄庭坚可以说“风流犹拍古人肩”,辛弃疾可以说“不恨古人吾不见,但恨古人不见我狂耳”,那是因为他们属于士人圈子,而且是士人中的名人——名士。尽管隋唐已逝,但他们和古人享有同一片文化土壤。可我们不行。科举制已经从根子上割除,我们与古人分处平行宇宙,很难站在自己的宇宙里,去拍那个宇宙里人的肩。
因此,想真正理解唐诗,理解唐代士人到底写了什么,又是如何写的,必须把他们放回到产生他们的土壤中去。这就是西川揭示的“唐诗的读法”。
2000年,诗人、翻译家黄灿然发表长文《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他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传统和西方现代诗传统,对中国新诗构成了两个巨大的阴影,每一位现当代诗人都会被拷问:你的诗比得上古典诗词吗?比得上西方现代诗吗?此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这么多年来,一直被反复讨论。不过按照西川在本书中的思路,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实质上被消解掉了——既然今天的诗歌土壤、作诗方式跟唐代完全不同,这种比较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与其说是现当代诗人的阴影,不如说是从未接受现代诗歌审美训练的大众,对于现代汉语诗不切实际的期待。
西川提出:“我们必须处理我们这充满问题的时代,并以我们容纳思想的写作呼应和致敬唐人的创造力。”我想,这正是本书的点睛之处。
作者:唐骋华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周怡倩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