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前的5.12汶川大地震时,我恰在离那里100来公里的地方带着一个百余人的团队在做一套大型丛书的营销推广活动,虽没有亲历那地裂山摇的惊恐,但大地强烈地晃动则是有了真真切切的体验,团队中也有被砸破了脑壳划伤了脚的。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身为四川省作协主席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朋友阿来在震后第一时间就赶过来安抚我们,而到了5月13日傍晚,他再次来到我们的住地,在看望的同时神色凝重地告知:因明天就要自驾进灾区救灾而没法陪伴我们了,于是只能互道珍重而依依惜别;两周后,阿来应我们之邀出现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参加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那里组织的部分作家义卖赈灾活动。
再往后,以5.12汶川大地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阿来这个四川的作协主席竟始终“缺席”。直到十年后的5.12,阿来才为《云中记》正式开笔。在谈到何以如此时,阿来直言:“我宁愿写不出来一辈子烂在肚子里,也不会用轻薄的方式处理这个题材”,“因为这作品如果没有写好,既是对地震中遭受灾难死伤者的不尊重甚至是冒犯,也对不起灾后幸存的人”。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定:阿来此前为5.12汶川大地震所做的种种只是在尽一个公民所承担的社会义务,而直到这部长篇小说《云中记》的面世,才是终于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位优秀作家为此而承担的文学责任。
据阿来自己裁定,这部《云中记》就是他“目前最高水准的小说”。既然如此,我也无妨坦陈自己的阅读感受。面对阿来这样一位认真严谨的作家,读他的新作,尽管每次都会在某一方面有所悟有所思,但这次读《云中记》所带来的情感与理性的冲击则是多方位的,无论是构思的精巧与严密还是情感的充沛与控制抑或是哲思的穿透与扎实都着实令人心动,这又谈何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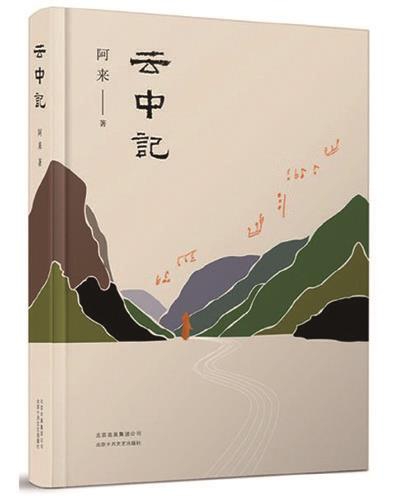
与5.12汶川大地震后随即陆续出现的诸多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同,《云中记》则是一直到距离这次人类大灾难十周年后方才落笔。这样的时间差直接决定了阿来笔下的5.12汶川大地震只能是历时性的回溯而不可能是共时态的追记,因此如何回溯、怎样结构就成了直接关系到这部作品成败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于是,在《云中记》中我们看到了阿来的智慧:处于震中的云中村在震后因其继续面临着次生灾害的巨大威胁,已不具备原址重建的必需条件。为此,云中村的幸存者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整体搬迁到政府在山下新建的移民村集体安置。然而,四年后,一个人、两匹马重新回到虽空无一人却充满大自然生机的村落,这个人就是云中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祭师阿巴。回村前,阿巴对移民村的乡亲们说:“你们在这里好好过活,我是云中村的祭师,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再往后,阿巴更是坚决地对自己的外甥也是乡长的仁钦说“我也要跟你分个工。乡长管活的乡亲,我是祭师,死去的人我管。我不要有那么多牵挂。”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以此为轴心搭起的历时性结构至少比那种共时性的追述具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阿巴在云中村的这一去一返使得作品对那场大灾难的回溯十分真切与自如;二是叙述的空间与传递的信息被大大拓展,在历时性回溯的同时还自然带入了共时性的叙述,于是,灾后的重建以及重建过程中的种种感动与变异同时得以呈现;三是阿巴这个人物的特殊角色和传奇经历决定了作品不可避免地引发对有关人与自然、有关生命、有关生存与死亡这些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
阿来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以5.12汶川大地震为题材进行创作,除去有些问题“没有想得很清楚”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因“情绪失控”而导致“没有节制的表达”。正是由于这种清醒,《云中记》总体上呈现出的确是一种平静的叙述和克制的笔触,但这并不妨碍这部作品情感的充沛,好几处的描写读起来催人泪下。比如乡长仁钦因默许自己的舅舅阿巴回到云中村而遭到县里停职反省的处理,比如在大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却又偏爱跳舞的央金姑娘回到云中村的种种表现,比如云中村大限来临之前阿巴的慷慨赴死、央金姑娘回到移民村、仁钦乡长面对隆隆滑坡体的内心活动……在这些场景的处理上,阿来的文字并不煽情,整个叙述调性平静而克制,但阅读体验则要么是怦然心动,要么是潸然泪下。我想这或许就是因阿来整个场景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相关情节的铺陈到位而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必然反应吧。

大地震、祭师,这种特定的场景、特定的人物角色,必然会触及人类与自然、生存与死亡这类世界共同面临的终极问题。当然也可以说,面对5.12汶川大地震如此惨烈的现实,文学除去讴歌灾区民众的顽强、抗震志士的英勇和全国人民的爱心外,是否还有值得进一步思索与挖掘的内容?而正是这样的问题苦苦萦绕了阿来十年,直到他有所心得有所感悟才刻意营造了这样的场景和这样的人物。而无论是哪种情形,《云中记》中所呈现出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则无疑是十分个性和极为深沉的。关于人类与自然,作品清晰地呈现出了这样一种逻辑: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庇护和资源,但它一旦发“神经”,人类就将面临灾难。因此,人类只要在这片大地上生存,那么在尽情享受自然恩赐的同时就必须承受它说不清什么时候就会发作的“神经”。人类提倡“环保”,固然可能减少大自然“神经”发作的频次,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抑制它。看上去这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但又何尝不是对自然规律一种冷静而清醒的认识呢?而关于生存与死亡,《云中记》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全部灌注在对阿巴这个特定人物的塑造上。这是一个“死”过两次的奇人,第一次面对“死”,身为电站管理员的他竟然奇迹般地生还,只不过一时失去了记忆;而第二次,阿巴则是面对被大自然击倒的众多亡灵以祭师的特定身份主动选择死亡。作品中呈现出阿巴的行为逻辑就是:活着的乡亲们有政府管,而那些死去的人我是祭师我就要管。于是,出于对家乡的眷念和对亡灵的关爱,阿巴毅然离开移民村孑然一身回到云中村与亡灵们相伴,在自己的行动中思考和悟透了生死,参透了其中的关系与秘密,于是面对自己最终的结局,阿巴的内心如此平静、行为那般淡定,这种向死而生的选择堪称进入了一种伟大的境界。姑且不论阿来这种思考的是非曲直,但称其为独特而深沉则绝对恰如其分。
一部《云中记》,地震、记忆、人心、自然、生命……一曲《安魂曲》,肃穆、沉重、庄严、壮丽、升华……这就是阿来在其长篇小说新作《云中记》中呈现出的多声部多色调。阿来说“这次写作其实就是记录一段我与那些受难的人们、小说中的人们共同的经历,记录我们共同的沉痛的记忆”,而我们则从这段记录中获得了超越记忆之外的更多更多。
作者:潘凯雄(知名文艺评论家)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范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