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精良的制作和上佳的表演等高配置来包裹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剧本,正在成为当下一些国产剧创作的“捷径”。这就好像是一道摆盘漂亮、调味丰富但食材不怎么新鲜的菜肴,乍尝之下也颇有滋味,但终归无甚营养。
由此便出现了一种新的需要关注的现象,即“精美、精致却不够精彩的剧”,其中以长篇古装剧为“重灾区”。《天盛长歌》的播出让观众大叹可惜“爱也难,弃也难,偏偏是部精致的烂剧”,《海上牧云记》因“注水严重”而被电视台退片,《鹤唳华亭》俄罗斯套娃式反转看剧体验“比搬砖还累”……为何画面精美、制作精良却反而遭遇“叫好也叫累”的质疑?这首先与国产剧开始逐渐告别粗放式制作时代有关——现在的古装剧几乎有了一套风格化的“国风”语法,从景别景深构图到考究的服化道,但也折射出古装剧在叙事上的短板。
这类“精致剧”的沉与闷虽拒斥速抛的爽,却终究不能真正地打动人
叙述短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剧情拖沓,二是叙事混乱。举例来说,“九州”系列剧《海上牧云记》有着打造中国版“中土世界”的野心,原著小说中“如军与潮北八部会战”二十个字,在剧中被抻长为五集、号称斥资一亿。而在同一导演执导的《长安十二时辰》中,剧情虽然提了速,然而节奏却乱了。“神童与临危受命的死囚联手,在十二个时辰内拯救长安”,一句话简介便引人入胜的故事,到了剧中,剧情每每要提起一口气猛冲时,便突然地自己泄掉半口,转而用大量“风情”冲散了叙事节奏。如上元节张小敬与人前往景寺途中遇到点烛行人,张便开始“导读”:“看见他们吃盐闻蜡烛了吗?这在长安流行很多年了……盐者,延也,烛者,寿也,吸足一根蜡烛的香气,这就叫吸寿烛”,很长知识,然而这段“风物大赏”没有引出任何案件线索,像是剧中一条突然的“插播”,难免生出出戏的违和感。

正如有观众所言,“如此炫耀是中了‘我很有知识’诅咒,又即‘我查到的资料一定要塞进台词’诅咒。”除了此类“缺少契机,飘在空中”的台词让人每每要跟紧节奏便会被卡出戏之外,还有一种台词属于创作者的故作高深。如正在热播的 《鹤唳华亭》,文官陆英在剧中感叹:“京城雪深啊,我们的储君恐怕还不如这鹤自由潇洒”,此时其女陆文昔接上一句:“唳清响于丹墀,舞飞容于金阁。鹤,实为猛禽,可以搏鹰!”确实在点题,然而仔细思忖却构不成有效的对话——毕竟这是台词对白而不是古诗接龙。
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即是观看疲劳——并非是“烧脑”产生的累,而是视觉刺激与头脑调用的不匹配性,即饱满画面和苍白叙事产生的落差。《鹤唳华亭》的“俄罗斯套娃式权谋”极具代表性:
主角:我设下一个这样的计谋。
反派:我看破了你的计谋,我将计就计。
主角:我知道你看破了我的计谋,也会将计就计,所以我根据你的将计就计来将计就计。
反派:我知道你看破了我的将计就计,也知道你会根据我的将计就计来将计就计,所以我也会根据你对我将计就计的将计就计来将计就计。

……
如此往复循环。剧情十分“忙”,然而高密度的节奏给出的却是失衡的信息量。“忙”都成为自说自话的“乱”,屏幕那头的观众并不能真切地共享这一份危急,自然也无法真的进入角色的世界、看到他们在命运里的挣扎、选择与人性,但这些才应该是经典剧作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经典剧作如《康熙王朝》《大明宫词》,前者式的正剧或如后者舞台剧质感台词,都并不会因题材内容、文白夹杂而使人感到疲劳,原因就在于此。
通常,以叙事见长的电视剧展示出风格化的画面往往是被赞有“电影质感”的加分项,这是对镜头使用的褒奖。当观众的注意力如同观影时一般高度集中时,满满的画面会调动观众更深地卷入故事,此时若剧情不能“拉住”人,尤其悬念与危机被“忙乱”的节奏稀释,无效叙事的着恼感就会被放大。对于已经抬高了期待感的观众而言,手中握住的线索缠成一团,高潮处突然哑了火,这类“精致剧”的沉与闷虽拒斥速抛的爽,却终究不能真正地打动人。
所以说,精美的包装只能是锦上添花的操作,却不能真正地雪中送炭,甚至可能将瑕疵更多地暴露。《海上牧云记》里“贵重”的航拍镜头虽精美,但与故事完全两张皮,既不服务于人物,也不作用于叙事,更像是“镶”浮在剧情的表面。《长安》中铠甲上的花纹雕琢精细,炫技般的操作力证作品细节精致。然而,长安街上的市井生活气息与崭新光洁的城楼格格不入。
精美包装,毫无力量感的故事,就像是沙堆出的建筑模型
今天,观众的审美正在快速升级,对镜头、构图、画幅等工业化表现都有着更为专业的渴求,并形成了工业化水平升级的驱动力。从表面上看,这些剧作在技术上十分过硬,其“精致”的皮相被认为是高度工业化的成果。然而所谓“高度工业化”,并不只有精良制作,而是首先以坚实的故事与逻辑为基础,在流畅而勾人的讲述中完成故事,其中深刻与意义不是干巴巴的主题先行或喊口号。制作上“过度包装”不能替代故事内核的坚硬,也无法完成真正有力量的讲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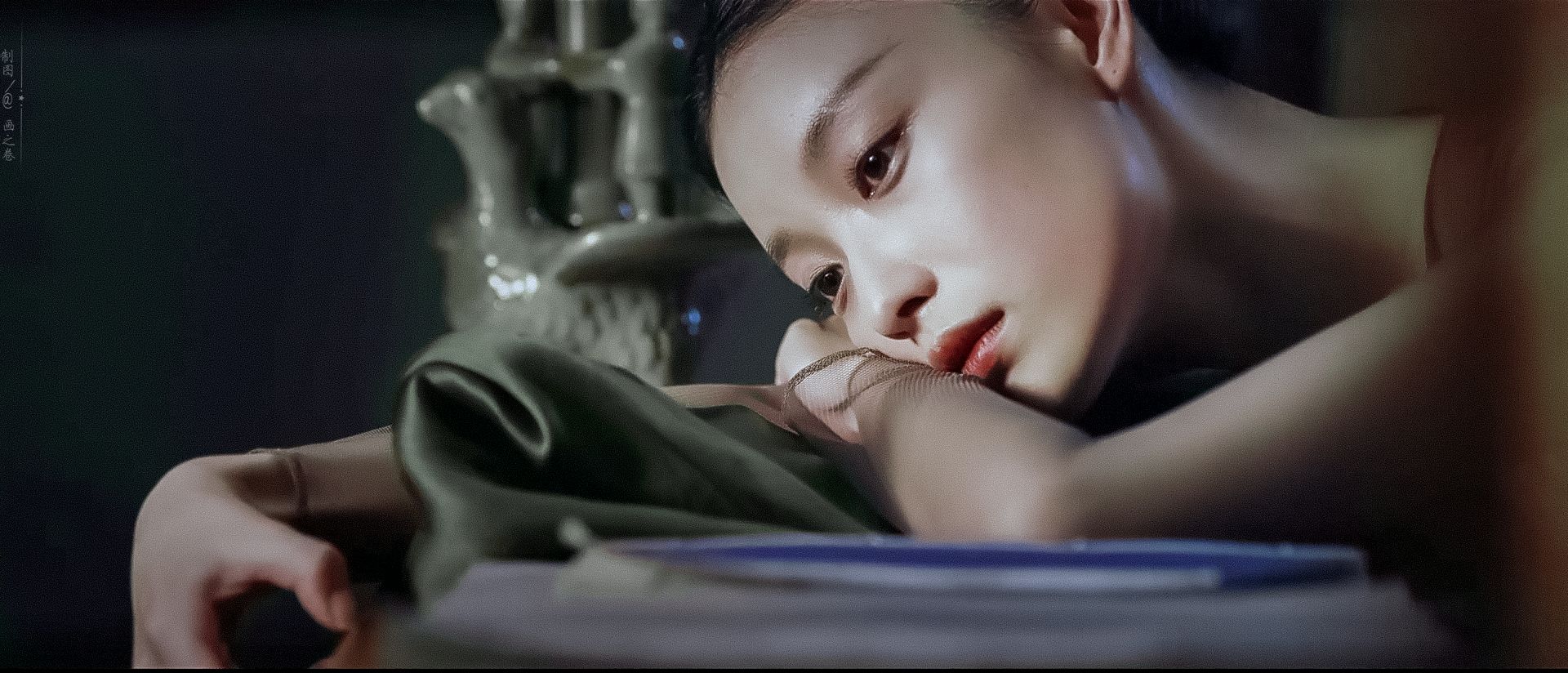
就拿《长安》原作“致敬”的那部海外剧来说,同样是一个24小时内“反恐”的故事,矛盾冲突、事件线索、多视角叙事,不仅有紧凑的节奏与巨大的有效信息量,完成事件后转场自然,人物行动线索清晰,并在一集的剧情内铺好反转,最终在制造视觉冲击的同时将人性的痛苦抉择直接拎到了观众面前。当危机出现,单数与复数的生命孰轻孰重?“应该撞死那个人吗”的电车难题拷问着每一个人。反观《长安》人物却稍显拧巴,同样的“救百姓还是圣人”的道德困境,在这里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直接塞给观众要救主。观众自然难免感到困惑:开篇伊始便铺垫大量情节立起来张小敬“讲道义”但“办事没规矩”的人设,最后却跳线到结局“卖队友”而“忠君救主”。人物内心的复杂与挣扎便显得十分做作,其所要表达的主题,也因人物的单薄扁平与状态的摇摆变得“可疑”、无法令人信服。
于是,配角被矮化为“工具人”,如同游戏中那些不受玩家控制的功能性角色,正义只在于主角的“天降正义”,而“正义”的逻辑也不是故事里生长出来的,而是硬塞给人物再由他们表演出来而已,其中原本可完成的厚重思考、故事本应有的复杂性,总会被“主角正义”的“设定暴力”所打断,被“真爱无敌”的鸡汤所牺牲。同样的,《鹤唳华亭》中君臣父子,家国天下的宏大追问,在剧情中也降级为“太子委屈,爸爸为何不爱我”的撒娇;还有《九州缥缈录》里无论主创如何硬性灌输也无法被有效识别的“英雄个人意志成长史”,都无法让观众对剧作力图传达的信念感感同身受。原因就在于观念本身的讲述,连自洽都困难、遑论取信于观众。精美包装,毫无力量感的故事,就像是沙堆出的建筑模型。

在今天,仍要强调“剧本作为一剧之本”与叙事,有其重要性与必要性。“讲好一个故事”其重要性高于“讲一个好故事”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内容的极大丰富,当媒体不再是稀缺性资源,电视剧这一题材最重要的竞争力正是取决于“如何说故事”。另一方面,电视剧区别于小说、电影、舞台等其他媒体艺术,“叙事”的要求内在于电视剧的“分散投入”特性中。如果说书籍是“选择性投入”,通常是“挑了一本书以后一口气就读完了”,而电影则是“强迫性投入”,在电影放映的一两个小时之内会被限制在某个空间里观看,电视剧的时长与播出方式决定了观众的观看投入度会相对分散,因此做剧必须将重点放在主要剧情的呈现上,故事永远是落脚点。
我们要做的是,精致、精美同时还可以精彩,国产剧的良心制作才能更上一层楼。
作者:韩思琪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读博士生)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范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