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修道文学对爱情和婚姻伦理的反思
(之三)
——彭小瑜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讲演
文汇学人 2014.3.3
明谷修院的贝尔纳:“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明谷的贝尔纳,另一位法国中世纪修道士(1090-1153年),在他的《<雅歌>讲道辞》和其他作品里也借助圣经里的这部情歌来发挥他对神与人关系的理解和见解。为什么中世纪修道院和教会作家需要借助《雅歌》直白、炽热、甚至性感的语言来描述人和神的沟通呢?亨利·泰勒在《中世纪心灵》一书里面曾经说,也许这是因为像贝尔纳这样的修士作家意识到,爱情和婚姻是最伟大的人际关系,夫妻之间的缠绵相爱,新娘和新郎之间“因思爱成病”,是他所能找到的最适合用来比拟人神关系的人世间景象。其实,由贝尔纳对婚姻的理解和描述可以看出,借助《雅歌》的话语,他把纯真的男女相爱看作是人世间最宝贵和最美好的画面:“我的良人,你甚美丽可爱,我们的床榻上撒满鲜花。”
修道文学的确长期有批评淫乱的传统,甚至有苛刻地责难爱情流荡的倾向。与休强调爱情之专一性一样,贝尔纳也提醒人们说,人的肉身需求,不论是情欲还是衣食的享用都不应该放纵滥用,而应该“控制在狭隘的范围”之内,如水流在渠道之内,使得物质需求不至于成为贪婪,爱情不至于成为肉欲之泛滥。那么这一“控制”的最起码尺度是什么呢?是爱人如己的对邻人之爱!对邻人的关爱,包括夫妻相互之间的体恤和抚慰,对每一个人自私自利的罪恶冲动是一种限制,使得人们不会让自我膨胀,不会让私利私欲驱动自己所做的一切。除掉这样的考虑,守贞的中世纪修士并不希望建设一个禁欲主义的、压制男女感情的世俗社会。相反,正如贝尔纳的研究专家勒克莱尔所指出的,12世纪的西欧修道文学作者已经很确定地意识到:“修士对天主的爱可以而且必须以人世间爱情的话语来表述。他们对天主的爱可以借助人世间爱情的形象和形式来表达、加强,这两种爱可以被整合为一体。”因此在这些修士的内心深处,对女性和男女爱情的看法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积极和肯定。由这样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贝尔纳对《雅歌》的解读中,人世间男女纯真爱情为何被浓墨重彩地美化,为何被高调地讴歌。
“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贝尔纳喜欢渲染《雅歌》里面提及的自然美景,以此作为他描写爱情场面的铺垫:新娘在田野里采摘果子和花束,让自己的身心和房间都充满花香和果味,迎接新郎的到来。在这“百鸟鸣叫的时候”,新郎招呼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在这样赏心悦目的美景中,在刻画新郎与新娘缠绵的情景时,“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样直白的句子被引用来描写的,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呢?除掉比喻信徒的灵魂与神的接近,贝尔纳也展开描写了一种脱离封建社会政治利害和经济利益的爱情和婚姻,尤其是在《<雅歌>讲道辞》第83篇里面。人尽管常有罪过,但是按照天主形象塑造的人也是尊贵的,人的纯真本性是善良的,人的纯真情感和行为可以让人的自然本性更加美好。此外,无论是休,还是贝尔纳,在西方家庭伦理传统的影响下,都倾向于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子女对家长的服从和敬爱并不代表最高层次、最纯真的爱,因为子女可能在敬爱父母的同时也有获取遗产和其他物质利益的希望,因此他们的情感可能主要是尊敬,而不是单纯的爱。只有夫妻,不论是新郎还是新娘,才把爱和忠诚作为唯一的追求。中世纪法律一般不允许妻子继承丈夫家的财产,妻子去世后她带来的嫁妆归她的子女,如果没有子女则返回娘家。
由解读《雅歌》出发,贝尔纳将理想的新郎界定为爱本身:“新郎就是爱。”夫妻之爱在中世纪文化里面通常被认为是强于父子之爱的:“这一夫妻关系比自然塑造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加强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与奴隶出于恐惧对主人的谄媚迥然不同,与雇员出于利益对老板的服从迥然不同,纯真的夫妻之爱只认知爱,而排除一切其他的考量:这就是新娘的爱,因为不论她是谁,她就是这样爱着。她唯一的财宝和希望就是爱。她充满着爱,而新郎因此愉悦满足。新郎不要求任何其他,新娘也不提供任何其他。这就是为何他是新郎,她是新娘。他们的爱无人能够分掉,甚至他们的儿子也不能。贝尔纳在这里引用奥古斯丁说,爱不需要原因,爱的果实就是爱本身。他在这里虽然试图阐释宗教意义上的爱,“我爱是因为我爱,我爱为的是去爱”,却觉得不得不以人世间新娘的爱来比喻:她抛弃一切其他的企图,她甚至放弃她自己,为的是全身心地去爱。因为新郎就是爱,新郎所求的惟有爱和忠诚,所以新娘应该做的也惟有全身心地去爱,而全身心的、纯真的爱就是完全和完美的婚姻。
这种对婚姻高度理想化的理解仅仅是修道人士的空谈或者宗教思辨吗?在修道院的墙外,贝尔纳和休对人世间实际的爱情和婚姻也发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作品往往成为大学生追捧的读物,还被主持婚礼的神父引用来教育即将结婚的男女青年和在场的所有教徒。英国国王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的宫廷曾经是世俗文学繁盛的园地,其中《猫头鹰和夜莺的争论》就可以理解为修道文学和世俗文学的一种交汇,无论是以神父口吻批评淫乱的猫头鹰,还是以爱情赞助者身份唱歌的夜莺,都痛惜夫妻关系的失和,痛骂勾引有夫之妇的恶棍,都认为妻子值得丈夫去体贴和关爱,一个粗暴粗鲁对待自己妻子的丈夫是不值一文的。尽管在中世纪欧洲社会,尤其是在贵族家庭里,联姻常常以财产和政治的考虑为重,但是修道文学和世俗文学在1000年以后逐渐明确地把感情看作是婚姻首要的因素。作为中世纪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丁甚至同情因为相恋而被处死的叔嫂保罗和弗兰切斯卡,意识到弗的婚姻完全是一场政治安排。他在《神曲》里面不得不把这对恋人放入地狱,但是让他们在地狱里面还依然相爱着。的确,在人世间,区分纯情和淫乱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启蒙运动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为了塑造适合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世纪欧洲的社会道德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嘲弄和批判,包括歪曲地理解修道文学当中的爱情和婚姻伦理观念。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7章里面指责修士们说:“他们严肃地抛弃掉当代的一切事务活动和欢乐;不饮酒、不吃肉、不结婚;折磨自己的肉体,损伤自己的感情,尽力过一种痛苦的生活,要以此来换取永恒的幸福。”
而实际的情况是,中世纪西欧修道院的清贫理想,因为教育人们摒弃贪婪,促成了对诚信和财富公益性的重视,使得西方传统道德在资本主义的严重冲击下,仍然不失为工商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基础;修士的守贞理想,因为批判淫乱,影响到了中世纪乃至现代西欧的世俗婚姻,教育人们珍惜夫妻间的心灵沟通和相互忠诚,帮助人们意识到真正的爱情不仅超越物质利益和家族兴衰,甚至超越男女间肉身的吸引和诱惑。在这样的文化和道德氛围中,赫利希教授所描述的中世纪婚姻关系革命及其肯定和推行的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不仅易于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也因为顺应人类对美好纯真爱情的追求而延续至今,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普遍接受的、主流的男女关系模式。
如果现代人厌倦了奢靡的生活风气,不妨读一点中世纪修士对爱情和婚姻的议论,也许因此会沉思、羞愧,开始新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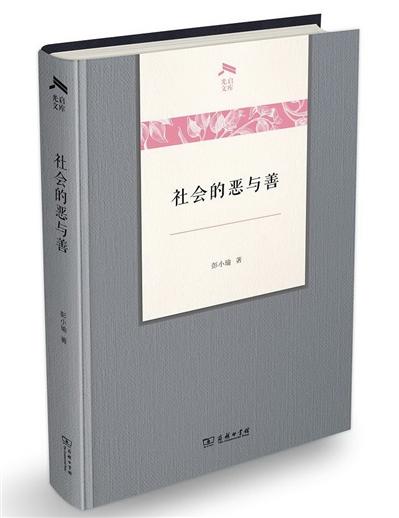
作者:彭小瑜
责任编辑:李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