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采来自透彻的理解:我心目中的翻译
——周克希在复兴论坛的讲演
(之三)
《文汇学人》2014.1.13
文采来自透彻的理解
翻译的文采首先来自对原文透彻的理解,来自感觉的到位。自己没弄明白、没有感觉的东西,是不可能让读者感觉到的。理解透彻了,感觉到位了,才有可能找到好的译文,才能有文采。
文采,并不等于清词丽句。文字准确而传神,就有了文采。好的文字,不是张扬的、故作昂扬的,不应是“洒狗血”,也不应是过于用力的。好的文字有感觉作为后盾,有其内在的张力(“黏性”)。即便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也难免有洒狗血的时候。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说:“(与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相比之下,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底气不足之感。”即便是周作人这样的散文大家,也难免有着力太过的地方。他有一段写废名的话很有名:“(废名的文字)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弯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再往前走去。”但还是汪曾祺,很中肯地指出:“周作人的序言有几句写得比较吃力,不像他的别的文章随便自然,‘灌注潆洄’、‘披拂抚弄’,都有点着力太过。”
回到翻译上来。译文要求准确、传神,落脚点还是感觉。举例来说,《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末尾处有一段描写布洛涅树林景色的文字。其中有一句我译成:“风吹皱大湖的水面漾起涟漪,它这就有了湖的风致;大鸟振翅掠过树林,它这就有了树林的况味……”(“大湖”是布洛涅树林中一个湖的名称,“树林”则指布洛涅树林)。原文是le vent ridait le Grand Lac de petites vaguelettes, comme un lac; de gros oiseaux parcouraient rapidement le Bois, comme un bois, ... “有了……的风致”、“有了……的况味”从字面上看是原文所没有的,但从意蕴上看确确实实又是有的。
但找准感觉并不一定是“做加法”。《情人》一开头,有句为不少读者所激赏的译文:“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语调低回而伤感。但在原文中,这是一个语气相当短促的句子(Très vite dans ma vie il aététrop tard.)。译文的感觉与原文出入较大,也许不妨改译作:“一切都来得很仓促,一开始就已经太晚了。”这样译,有点“以短促还其短促,以枯冷还其枯冷”的意思。
感觉不同,用词的色彩自会不同。《包法利夫人》中写到elle s’enflammaitàl’idée de cette taille si robuste et siélégante, ... 我没有译作“她淫心荡漾,按捺不住地想到另一个男子”,我觉得那种译法的强烈贬义色彩,是原文所没有的(按照福楼拜的创作原则,他也不会那么写)。依据我所感觉到的作者的意思,我把这个句子译作“她心里像烧着团火,如饥似渴地思念着……”。有的词很简单,感觉却并未必简单。比如,福楼拜写到爱玛被罗道尔夫抛弃后,大病一场。养病期间,每天下午坐在窗前凝神发呆,“其时,菜市场顶篷上的积雪,把一抹反光射进屋里,白晃晃的,immobile,……”最后那个词,有译成“雅静”的(“一片雅静的白光”),也有译成“茫茫”的(“一片茫茫的白光”),但在我看来,那样的译法,似都仅与光线的状态有关,而与爱玛的心态无涉。在我的感觉中,那是一种“以外写内”(即以外在的动作、状态,来描写人物的心理)的手法,所以我把immobile译作“凝然不动”。这是我对光线的感觉,也是我对爱玛心态的感觉。
更极端的例子,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从引入中学教材的译文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若……则……”、“∵(因为)……∴(所以)……”这种源自简洁、准确的文采。更一般地说,数学语言,常会让我为它们的美而心折。我常举的例子,是极限的定义。极限,这么一个看似谁都明白的概念,困扰过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最后,法国数学家柯西(Cauchy)终于给出了严格的极限定义,为数学大厦奠定了坚实基础。那短短两行数学语言,在我眼里几乎是人类语言美的极致。
当然,数学语言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们被用于数学的领域。我从数学改行,从事文学翻译以后,心里时时在警惕:有两种腔调要尽量避免,那就是数学腔和翻译腔。其实,还有一类词也是要避免的,那就是“通过”、“根据”之类的文件用语。这类词自有它们的用武之地,但在文学翻译中,我想应该慎用——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不用这类所谓“大字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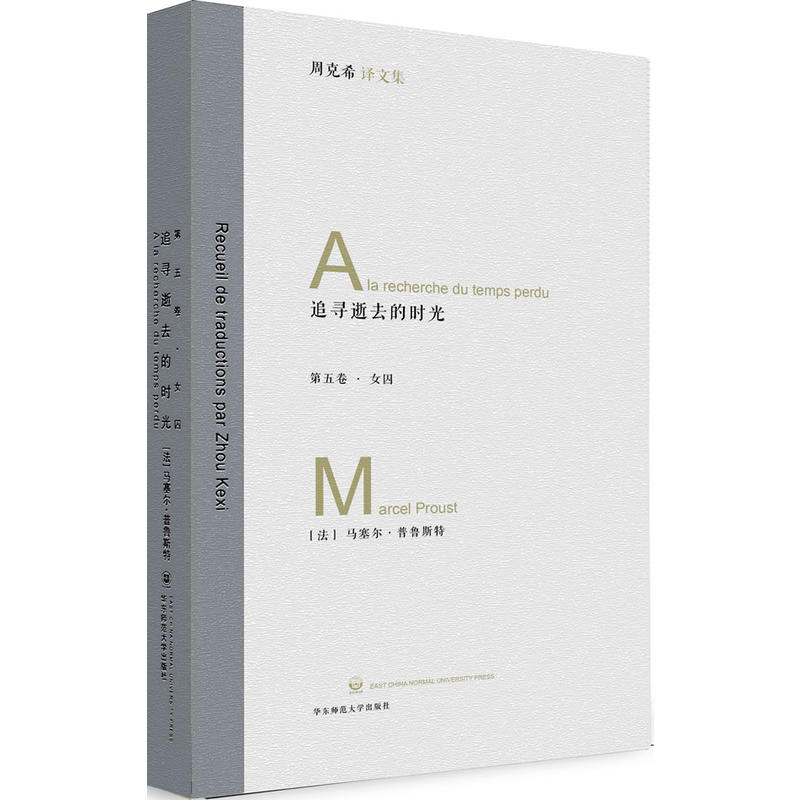
作者:周克希
责任编辑:李纯一





